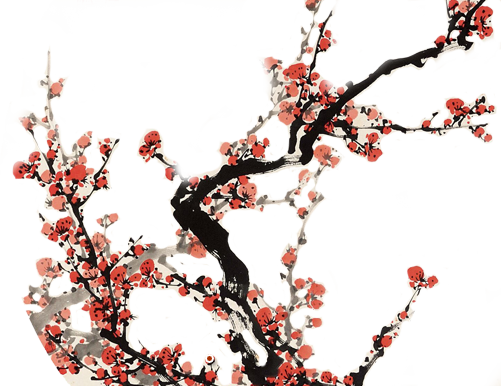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认识王充闾已经20年了
石 杰
记得好像是1990年的冬天,天冷极了。我和当时学报的老主编一起,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到省城去办一件公事。原以为事情会比较顺利,没想到竟卡了壳,于是,经老主编的同学引荐,我们便一起去拜访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充闾。
当时王充闾好像刚上任不久,家还没有从营口搬过来,他是在办公室里和我们见面的。不用说,心怀“鬼胎”的我和老主编都有些尴尬。我趁着老主编和王充闾说话的当儿,不时地四下打量着,偌大一间屋子,除了靠窗处的一张大办公桌,一把椅子,和挨墙放着的两个文件柜,此外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这使得整个房间显得特别大,也特别安静。老主编显然已经改变了主意。也许是初次见面不好开口,也许是觉得为这点儿小事打扰省委领导不好意思,总之,他绝口不提我们此行的真实目的,只是谈些文学上的事,倒好像是一位真正的拜访者,专程来访这位身居政界的文学家的。
那时王充闾正值创作盛年,已经出版了《柳荫絮语》、《人才诗话》等几本集子,在文坛也有了一定的名气。一些著名学者、评论家都注意到了他的散文的价值和独特的风格,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就连我们这个小小的学报,也收到并发表过几篇关于他的散文创作的评论文章。在我的想象中,一位副省级官员,即使修养再好,也难免会有些官气的,不可能像普通百姓那样便于接触,然而坐在我们面前的王充闾却始终那么平静,那么谦和,那么自然,有时专心听老主编说话,有时问问下边的情况。仿佛相交已久的老朋友一般,没有一点儿高官的架子。我望着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听着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看着进出人员来去匆匆的身影,心里始终缠绕着一个疑问:官做到了这份儿,怎么还偏要搞创作呢?这种环境哪有功夫写作啊?而且不知不觉就溜出了口。想不到这普普通通的一问,竟成了我们日后交往的源头。十几年后,王充闾仍然深有感触地说:“是啊,置身文山会海,位子也不算低了,为什么还独独钟情于文学女郎?这是一位大学教师第一个提出来的。”那时的我实在单纯幼稚得可以,总以为文学是为普通人预备的,不平则鸣嘛,不知道高官也有高官的苦痛。现在想来,那简单的一句话,很可能牵动了他心中的肯綮。
这之后,我们渐渐有了些来往。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特别“清”,不喜欢和世俗打交道,对文化、人才却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爱,好像他就是为文化、人才而生的。听说当年有一位青年作者写了一首诗,投了几家报刊,就是无人发表,一气之下直接寄给了王充闾。王充闾看后,觉得水平相当不错,马上推荐给一家报纸。这样的事,现在恐怕想都不敢想了。还有一次,我和市文联的同志陪同他一起去闾山寻访萧太后墓。进山前,听说某文化部门新近弄来一些木化石,就一起去看,果然,化石林很是整齐、壮观,到跟前才看出是经过黏合处理的。王充闾当即批评负责人不该这么做。他说:“这些东西就是历史的见证,原来啥样就啥样。你把它人为处理了,看着好看,实际上价值削减了。”那时他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我们都担心他这样兜头泼人家一瓢凉水会让人难以接受。现在看,他是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感出发说话的。
我多次和他交流过对文学、人生的看法,读过他不少诗文。尤其是前几年写《王充闾:文园归去来》这本评传式理论著述的采访过程中,对他的了解可以说更全面、深刻了。他5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之后做过教师、报纸副刊编辑,后来便在省市领导机关工作。这是一个头脑异常清醒的人,有热情、才情,更不乏理性。他总是客观地分析别人和自己,从不会被来自外界的各种各样的赞扬、吹捧冲昏头脑,迷乱心性,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记得90年代初有一次开他的散文研讨会,慕名而来者很多。大会开始之前,他忽然发现会标上写的是“著名散文作家、诗人王充闾创作研讨会”,当即和有关人商量,坚持去掉“著名散文作家、诗人”几个字。他说:“我还算不得什么著名作家、诗人,不要搞这种花架子。”就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他也比较低调,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明智,可以说是他的性格中的最大特征。
王充闾的清醒、明智不仅表现在客观求实、不慕虚名上,也表现在对官与文的不同态度上。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起,他就走进了市委领导机关,而他从事文学创作比这还要早十年。除了“文革”期间被迫停职、辍笔外,他一直是一手搞行政,一手搞创作,而且两者都颇有成效,可以说是典型的“鱼与熊掌”兼得。那么他对官与文的态度如何呢?或者说二者在他的心里是否一般轻重?我觉得还不能这样说。诚然,他为官的名声、政绩都确实不错,有人称他做省委宣传部长的工作是“四两拨千斤”,也并非完全是夸赞之词,然而我总觉得他在官与文之间,更看重文。为什么呢?因为官比文更有永恒性、不朽性,更能让个体人的生命从有限进入无限。
王充闾是一个特别看重个体生命价值的人,如何使自己的人生不虚度,实现它最大的价值、意义,是他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他曾多次慨叹庄子、陆游、苏东坡等古人之所以流芳百世,原因不在官职,而在文章;尤其李白,好多人都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官,可是,他那才华横溢的诗,却万古流芳、家喻户晓。时下人舍命追求的权势、钱财在他眼里都是有限之物,没有多大意义。他在本世纪初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散文论坛”演讲中就这样说过:平时颐指气使、势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到头来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一死,同穷光蛋又有多少差别!可见他搞文学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像有的官员那样,弄本书附庸风雅,在官员的身份之外再贴张文人的标签,而是在实现生命的价值、延展生命的长度、扩张生命的时空的角度来追求的。否则,他的笔早就在繁忙的公务、眼前的利益中搁下了,更达不到现在这么成功的地步。
也许有人觉得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儿太玄乎了,或者干脆就是不可思议。其实说白了,这也就是一种理想精神,只是时下怀有这种精神的人越来越少了,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所以,当下人活得浑浑噩噩;所以,某外国学者断言: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而当我以“清醒”、“明智”来定义王充闾这种所思所为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贬低或者拔高,而是含有一种人如何活的问题的问题。当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为什么活,怎么活,的确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否则便很可能应了老百姓常说的那两句话:“后悔就来不及了。”“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王充闾确实称得上是个智者,不但敏于感悟,而且勤于思考,喜欢在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上体悟、发掘出不同寻常的东西。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游记散文中,这一点就突出表现出来了。比如参观萧红纪念馆,他感叹这位离世不到半个世纪的女作家,名气和身后所留之物之间的差别竟然这样悬殊;出差南京,本来第一眼就想看看秦淮河,无意中得知秦淮河早在民初就已经破败萧条,绝非朱自清笔下那般如梦如幻、如诗如画后,立刻打消了寻访的念头,宁可“在记忆中永存它的倩影”,也不愿那美妙的景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黯然消逝;与友人按图索骥、畅游闾山后竟觉得意兴阑珊时,他不由得联想到当年游览绍兴遗下鉴湖,此后一直心向往之的感觉,得出了“人们对于已经占有、已经实现的事物,不及对于正在追求、若明若暗、可然可否的事物那样关心”的哲理性结论;耳顺之年重过落红成阵的桃林,却再也找不到少年时经过此处的兴奋之感。由此又联想到人们常常用回忆、摄影甚至全息影片来保留当年情景的做法,于是深深概叹:“年光已经飞鸟般地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由后人去指认、评说。”
到了90年代后的历史文化散文,他又把知人论世的习惯移到了历史人事上,认为李白在文学上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仕途的受挫,而仕途受挫的根本原因又恰好是因为他诗人的资质;曾国藩的人生表面看是成功的,实际则是失败,因为他过于追求完美,谨小慎微,活得太苦、太累;端坐龙椅的皇帝虽至高无上,到头来仍难免事与愿违,难逃命运的捉弄;只有像庄子、严光这类高人、隐士,淡泊名利,超凡脱俗,才能活得逍遥自在,得养天年。
这种智者的思考显然与一个人的知识积累有密切的关系。王充闾六岁进私塾读书,先是“三、百、千”启蒙,继之四书五经,诗古文词,可以说从小就被引进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海洋。他嗜书如命、博闻强记,几十年中,无论古今中外、文史哲社,都在他的阅读范围之内。我曾有幸见过他那四壁图书,摩顶接地,挤挤挨挨,大约总得有上万册吧。记得我曾这样问他:“您跟死神打交道的那些日子里,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就是我那些书啊。”他毫不犹豫地说,“我要是死了,那些书可咋办呢?”书给了他知识、智慧,官员生涯又让他开阔了眼界。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回想着他总计四十多年的创作、面对着那洋洋几百万字的作品时常想:所有这些文字都在说什么呢?有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核心的东西?尽管对于散文这种文体来说完全没必要这样分析?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他其实一直在探索人、人生、人性、人的命运,尽管时常以史、事、景的面目出现,但都在思考人,思考人为什么活,怎么活,活得怎样。这是他写作的动力,也是他的散文让读者们喜欢的根本原因。从这一角度说,他确实有一种哲学家的能力和素质。
王充闾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可是你不仅从外表上看不出他的生理年龄,就是内里的生命热情也不减当年。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创作了,除了“文革”十年被迫停笔外,一直孜孜不倦地读书、写作,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就连“文革”,他也没完全放下书本。他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追求,真是到了忘我的程度。虽然如此,我却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表面看,他自信、坚定、从容、镇静,骨子里却含着深深的悲观和无奈。这一点,除了天性,可能和他小时候的遭遇有关。
他祖籍河北大名府,祖辈逃荒流落到素有南大荒之称的原辽宁盘山县。他本来排行第四,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可是哥姐都在他童年时去世了。他在《母亲的心思》中曾经这样追述:“姐姐大我二十二岁,也非常聪慧,由于受家庭影响,从小读了许多文学作品,一部《红楼梦》……读过七遍,每番读过,都是泪湿衫袖。姐姐在我两岁时,不知患了什么病,早早地故去了,”剩下一个两岁的女儿,寄养在母亲的膝下。不久就是他的二哥。“二哥大我十六岁。他还在读书时,就写得一手潇洒、俊秀的赵体字,三间屋里每面墙上,都有他的墨迹。”不幸的是年纪轻轻,就被结核菌夺去了性命。最可惜的是他那已经成为家里的顶梁柱的大哥,只是偶然患了疟疾,不用药也会痊愈的,却被庸医误诊为伤寒,下了反药,倏然间就去世了,想得他的父亲每天扛着铁锹到儿子的坟头转悠,盼着儿子能活过来。不久,感情上像母亲一般的嫂嫂也带着孩子改嫁了。尽管这一切发生时王充闾年纪尚幼,心智还不成熟,只能凭着本能接受周围的一切,但早慧的心已经感受到了那种凄凉,何况童稚的心灵也缺乏抵抗苦难的能力。
半个世纪后的身患重症,对他的打击显然更为沉重,那可是切切实实地关涉到了一个人的生与死。记得当时我从他的一个同学口里听到这意外的消息后,便打电话问候,安慰他说佛祖会保佑他的,因为恍惚记得有一次他说过释迦牟尼是大彻大悟之人。电话那边,他凄然一笑,顺嘴吟了一首诗,大致是:“寻佛问祖到山腰,风摇大树撼早潮。八八减二无常数,到底人间一粒消。”可见他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沉重、无奈。他将手术后一段时间的情形比喻为头上悬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说不定什么时候,那根马鬃一断,剑就会落下来,取了他的性命,幻灭感也由此蓦然而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觉得一切希望与抱负都失去依托了,“一时间,困惑、忧郁、浮躁、压抑、焦虑、恐惧、失望、悲伤,铺天盖地而来。”
当然,悲惨遭遇和悲观主义之间未必就该画等号的。一个一生坎坷、不幸的人,未必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反之,一个终生顺遂或稍有不幸的人,也可能持有悲观主义信念。个中的原因,还是与“识”有关,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智慧。或许是多年身居领导阶层的缘故,王充闾很善于控制内心的情绪,但是,只要我们仔细体味,就不难发现,他的散文几乎从一开始,字里行间就蕴藏着悲感,我称之为“识”。他感叹人生短暂、韶华易逝。有情人难成眷属。人的欲望太多而能力有限。现实永远比不上想象中的美好,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永恒的距离。所有的存在都是不确定的。历史无情,规律无情,到头来,宇宙千般、人间万象,都会被历史老仙翁收进歪把子葫芦里。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只能在痛苦中挣扎,逃不脱悖论的魔爪。事实上,王充闾是在以他的智慧和奋争,与悲剧性的人生对抗。
这种情形,很容易使人想到神话中的西西弗推石头上山。西西弗的悲剧在于他对自己的命运有清醒的意识,或者说,清醒的意识才是人的悲剧不可缺少的前提。“西西弗,这诸神中的无产者,这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他完全清楚自己所处的悲惨境地:在他下山时,他想到的正是这悲惨的境地。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成了他的胜利。”这段话,是加缪在著名的《西西弗》神话中说的,用到王充闾身上,也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