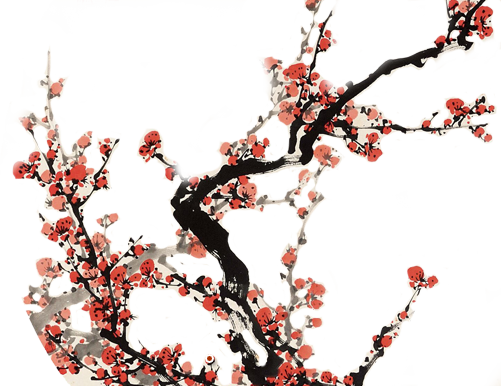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叩启鸿蒙
一
佛经上有“浮屠不三宿桑下”的说法,为的是在一棵桑树下面连续住上三宿,僧人会产生眷恋的情怀。
也许事实果真是这样。“黄莺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四五声。”——唐诗中如是说。鸟犹如此,号称“感情的动物”的人,自然更不必说了。
我就有这样的实际体会。近日,在贺兰山下住过了几天,一种流连忘返之情渐渐地潜生心底。
这里地处流光溢彩、飞金洒银的河套平原,贺兰山绵亘数百里,宛若一列壁立千仞的天然屏障,拦阻了西面蒙古高原的卷地风沙和凛冽寒潮;东面是南北流向的滔滔滚滚的黄河,连同开凿于一两千年前的秦渠、汉渠、唐徕渠,为浩茫无际的沃野平畴输送了川流不竭的充足水源。所以,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的民谚。
眼下正值“天凉好个秋”的丰收季节,连续多日都是弹得出声音、照得见身影的响晴天。金黄的稻海浮荡着万顷微澜,把一个偌大的银川平原装点得光华灿烂;山麓、草场上游走着一群群雪团、棉絮似的身躯臃肿的肥羊。与展现在高远无垠的湛蓝天宇上的层层片片的云罗霞锦,上下交辉,遥相映衬,织成一幅丽景天成、悠然意远的图画。
应该说,这里的山川确实雄浑壮美,大地也是富丽丰饶的。然而,我之所以宛转低徊、流连无限,却并非着意于此。真正使我动心动容、感发奋起、兴会淋漓的,乃是贺兰山的岩画,——这形成于混沌初开的鸿蒙时代,被称做“人类早期艺术的活化石”,“游牧民族用艺术形象描绘的史诗”。
对此,早在公元五世纪,我国北魏学者郦道元就在他的名著《水经注》中作了记载:黄河所经的石山上,“悉有鹿马之迹”,“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
贺兰山岩画属于北方草原文化类型,是由不同的游牧人群按照不同的心理意向,先后凿刻在绵延数百里山崖上的文化遗存。经“地衣测年法”鉴定,岩画的制作时间上自远古狩猎时代,下迄宋、元与西夏末叶,跨度将近万年。已经炸毁、剥蚀的不算,现今尚存五千余组,个体形象多达数万,最大的画幅长十余米,最小的仅一、二厘米。穷形尽相,光怪陆离,构成了一个含蕴无穷的造型艺术的大千世界。
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岩画从开始诞生,就紧密地同人们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交织在一起。可以说,每一组岩画,都闪现着远古先民智慧的灵光,承载着他们在大自然面前既无能为力又并不甘心的痛苦抉择,记录着他们筚路蓝缕、与时共进的艰辛历程。
二
此刻,我正站在一幅构图奇异、耐人寻味的岩画前。
画面上,左右两旁各有一个左手印,左边手印下刻着一只低头的山羊和一只前腿下跪的牛,右边手印的上下方各有一个人面像。两只手印的中间站着一个双臂扬起的人,上面的显著位置刻有一个环眼圆睁的桃形人面像。画图十分生动有趣,可是,它的意蕴究竟是什么呢?端详了半晌也未得其解。
后来经过向专家请教,才弄清楚原来这是一份具有“契约”性质的文件,——以岩画的形式确认了古代两个部落之间的隶属关系。手印是象征着权力的。左边那个部落已为右边部落所征服,随之它的人口与牲畜也全部划归右边部落所有。桃形人面像象征着神祗。有神、人共鉴,石画为凭,这份“契约”自然具备着无可置疑的效力。
在向阳的山崖斜坡上,我还看到一幅凿刻得很精致的射猎图。画面上,一个人正在弯弓射箭,七只硕壮的山羊惊惶逃窜,其中五只向东奔跑,两只向西逃逸,而猎犬却回身伫望着主人。猎人形象凿刻的很小,表明他所在的位置距离羊群较远。由此可以看出,那时的先民已经注意到了运用透视关系来进行构图处理。也说明,在很古的时代,水草丰美的银川平原就已成为各游牧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劳动创造、游牧狩猎的理想乐园,也是各种家畜和野生动物的繁衍、栖迟之所。
一组游牧风情图的宏大画面上显示,牦牛、骆驼、花斑马、梅花鹿、北山羊散放在原野里,有的在欢乐地角抵、奔逐,有的静静地低头吃草,有的在悠然闲卧。旁边站着一个游牧人,顶上的头发盘结起来,腰间斜插着一根木棍,胯下拖着一条又长又大的尾巴。身后跟随着一只猎犬,懒洋洋地呆望着主人。画图的右边,聚集着一队歌舞腾欢的人群,男人头上有的装饰着兽角,有的插着羽毛,有的戴着尖顶或圆顶的帽子;女性则长发下垂,也有挽着发髻、装着头饰的。场上,翩翩的舞影,忘情的啸歌,衬着多姿多彩的穿戴和装饰,渲染出原始艺术粗犷、质朴的特色。
为浓郁的生活气息所吸引,此刻,我也仿佛置身其间,随着欢乐的人群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尽情尽兴,和先民们一起发出欢腾的吼声。此间,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大自然焕发出勃勃生机。丛林掩映中,一些平生未曾寓目、而今多已灭绝的动物蹿跃其间;一队前额低平、眉骨粗大、目光迷惘的人群,正在咿唔呼啸着追奔射猎。回望山崖,发现那里还有一些人在紧张地劳作着。趋前细看,他们手持石刀、铁錾,或凿、或敲、或磨、或刻,正全神贯注地制作着各种人面和动物的图象,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他们的手下赫然展现出来。……
我正在忘情地欣赏着这一切,不料,稍微一愣神,忽然发觉山崖上的人形已经淡出、隐没了,逐渐逐渐地幻化成山垭口处一伙凿石垒渠的人群。伴随着各种敲击的繁响,一道清溪从山坳里冲出,顺着渠道滔滔汩汩地流淌下来,顿觉遍体生凉,神清气爽。于是,我也憬然惊寤了。
心头的意念一收,时间的潮水,哗—哗—哗,一下子流过了几千年,我也随之而返回到现实生活里。
三
贺兰山岩画本身就是一部文化传承的史书。它是地处祖国西北的许多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现在,人们一提起银川,就把它同西夏联结起来,漫步街头,随处可见“昊都大酒店”、“西夏贡酒”、“昊王宫”等与西夏王国有关的商标、名号,这固然有其重要的依据。但是,严格地讲,它仅仅是一部份,而并非全体。
早在数千年前,就有许多少数民族在这一带游牧、畋猎,繁衍生息。见诸史籍的,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贺兰山下主要游动着猃狁、羌、戎等部族;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先后有匈奴、鲜卑、氐、羯等族;隋唐两代,突厥、回鹘、吐蕃等族聚居于此;迨至两宋、西夏时期,这里主要是党项族;元代则为蒙古族所领有。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跃上历史舞台,次第更迭,薪尽火传,演出了一幕幕威武悲壮的历史活剧。
随着时序的推移,他们有的迁徙了,有的变化了,有的消失了,像成群结队翱翔于万里秋空的候鸟一般,忽剌剌地飞来,又急匆匆地逸去,许多重大活动,文字都没有记载,甚至煌煌正史上也尽付阙如。事实上,当然并非落地无痕,杳无踪影,而是一站接着一站传承着社会文明的熊熊爝火,为建构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传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遍布贺兰山上,由五千多组岩画连缀而成的艺术长廊,就是绝好的历史见证。
我们怎能不由衷地感激那些伟大的民间艺术家——成千累万的无名的岩画制作者!是他们以其独特的艺术创造,为后世人民留存了形象鲜明、信息丰富的时代屐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研究古代文明史的第一手资料。
高尔基说得好:“人,按其本性来说,就是艺术家。他无论如何处处力求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美。”游猎的先民在浩瀚无垠的荒原上,通过与大自然的艰苦拼搏,培植了粗犷豪放的性格,也播下了信念、追求与热望。他们在呼啸、奔逐、游牧、畋猎之余,借助于岩画的创作,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忧思感奋、所见所闻一一凿刻于山石之上,以获取心理上的满足与快感,达到抒发情感、愉悦身心、恢复体力、消解疲劳的作用。
岩画开创了人类艺术的先河,是一部融汇着理性与野性、现实与幻想、稚拙与灵动的无声的交响乐。同时,又是一个活的解释系统,它无异于一部古代游牧民族的百科全书,向后人展示着先民对于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的认识,把他们敬仰的神灵、崇拜的图腾、朦胧的遐想、放牧狩猎的经验以至于七情六欲等深层次的内涵如实地记录下来。
四
黄河,这祖国的母亲河,历史之河,文明之河,在她的身边,岩画与神话并存。它们作为人类精神活动、艺术实践的智慧之果,都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本原的沃土之中。那些借助于想象与幻想,把自然力加以拟人化,反映远古先民对于世界起源、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神话传说,在贺兰山岩画中同样有所展现。
关于伏羲、女娲这两位始祖神的传说,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古籍,同时,广泛流传在黄河流域一带的民间。与两位始祖神“本为兄妹”、“蛇身人首、尾部相交”等传说内容相对应,贺兰山口一幅极为古老的岩画上也有他们的造像——人面蛇身,共同交尾于一条长蛇之上。画像要早于伏羲、女娲其他造像几千年,极为简单、原始,却是鲜活动人。
就一定意义上说,神话原是某种风俗、习惯、信仰和宗教的反映;而岩画则是从艺术的角度予以形象的记述与描绘。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山海经》中有关“戎,其为人,人首三角”的记述,实际上,指的是人的头顶上的兽角装饰,贺兰山口的人面型岩画中就有这种头戴三角的装饰形象。岩画与神话互为印证,表明古代一个时期西戎族的先民曾在这一带生活过。
《史记》和《竹书纪年》中都有关于“感生神话”的记载,如说周始祖后稷之母姜 在野外见到巨人的足迹,心忻然悦,践之,遂有身孕,及期生子。这在岩画中亦有所反映。据专家解释,所谓“践巨人足迹”云云,原生状态乃是一种生育舞蹈动作,——男女相伴而舞,踏着轻盈的脚步,然后野合作爱,从而得怀身孕。贺兰山的岩画就是这样表现的:在一对脚印旁边,一双男女在纵情地狂欢、跳舞、拥抱,集中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于生育的崇拜与渴望,以艺术形式给予“感生神话”以精彩的图解和印证。
原来,原始人的思维处于人类思维的童年形态,带有“巫术性”的成份。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是一个相信万物有灵、凡事迷信前兆的世界。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受着超自然的力量支配,诸如日月的升沉,四时的更迭,草木的荣枯,动物的繁殖,人世的生老病死、穷达休咎,背后都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操纵着。他们既满怀畏惧,却又不甘心任其摆布,总想通过一种特殊的行为来影响它,利用它,于是,便产生了巫术。
在先民的心目中,岩画中的动物就是生活中的实物。因此,只要在山崖上凿刻出交媾与生殖的画面,就能实现人畜兴旺的愿望。同样,为了扩大狩猎的战果,便在岩石上不厌其烦地制作着大量的动物图形和游猎场面,他们确信,只有把动物的形象画在山石上,(有的还要用箭镞射中它,)才会产生游猎预期的效果。
看着这些千奇百怪的画面,也许有人会觉得它们过于粗糙、简单,甚至荒诞无稽。可是,远古的先民正是凭借着这些普通至极的线条与符号,描绘出了整个的万有世界,一如音乐的七个音符,可说是再简单不过了,靠着它们却能谱出情动三军、绕梁终日的万曲千歌。
五
当然,也无庸讳言,作为史前社会的文化遗存和符号系统,作为图腾艺术的物化载体,贺兰山岩画尽管意蕴之深邃、视野之闳阔为世人瞩目,但它们全由图象组成这一共同特点,却是振古如兹,一成未变的。千年前的也好,万年前的也好,线条、画面、构图、命意,几乎看不出太多的变化。无论其为象形图式,表意图式,还是情感图式,都一无例外地以图象寄寓意义。单就“不确定性”这一点来说,与文字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历史在这里似乎经久地原地踏步。
时间在这里似乎凝固了。
人生易老,年寿有时而尽,对于时间的飞逝,现代人总是特别敏感的。几度花飞叶落,一番齿豁头秃,常使人感慨重重,蓦然惊悚。
当年,党项族的首领建立大夏国之后,仿照中原王朝的模式,不仅在都城和林峦佳处建起了金碧辉煌的玉宇琼楼、离宫别馆,还选定了贺兰山东麓为其历代君王夜台长眠之地,在五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留下了数百座大大小小的“金字塔”。
时间仅仅过去了几百年,于今,当日的千般宏丽,万种豪华,已经踪迹无存,只剩下几盔荒冢、数堆瓦砾,萧条破败,零落在秋风里。相反,当人们面对这些“粤自盘古,生于太初”的岩画,——这些远古游牧时代的文化遗存,想到它们阅千古而长新,历万劫而不磨,神奇地存留到今天,又怎能不为之而感到惊异、感到庆幸、感到振奋呢?
可以说,解读岩画就是在叩启鸿蒙,等于翻检一部已经失传了的史前典籍。画面上的犀牛、野马、北山羊、单峰骆驼等珍稀动物,不是在一两千年前就已绝迹了吗?而那幅岩画上的大角鹿,据古生物学记载,原是百万年到一万年前的远古孑遗呀!沧桑迭变,岩画长新。时间峻厉无情,然而却又是万分公正的,它善于选择,它并没有吞噬一切。
时间,时间,我们现代人在这里真正感受到了时间!
当年,大诗人白居易曾经一往情深地咏赞西湖:“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现在我却要说:“未能抛得银川去,全部勾留在此图。”
通过解读这些变形夸张、耐人寻味的岩画,不仅获得一番值得永生忆念的艺术享受,而且,接受了一次认识生存根基、启发生态自觉意识的教育,——拨开重重的朦胧烟雾,可以重温人类蒙昧时期的宿梦,聆听远古历史微弱的回声,透视原始先民与生物环境同生共存的真实景象,进而悟解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链中的恰当位置,克服诛求无限、为所欲为的狂妄心态,真正实现回归家园、认清本源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