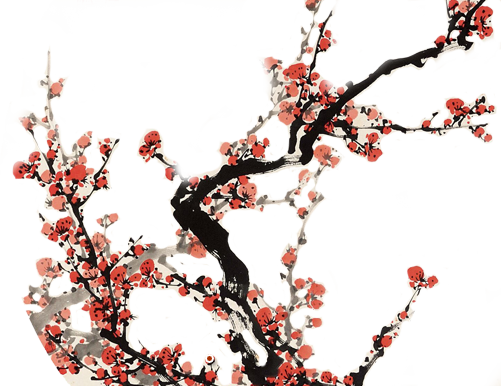土 囊 吟
王充闾
一
幼年就从史书上知道,在东北的苦寒之地有个五国城。可是,只因为它太偏远、太闭塞,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有机会踏上黑龙江省依兰县的这块土地。
公元十世纪,分布在依兰以东、松花江和黑龙江沿岸的“生女真人”,形成了著名的五大部族,通称五国部。这里是五国部之一的越里吉部的驻地,位置在最西面,当时是五国部的会盟所在,故又称五国头城。古城遗址在县城北门外,呈长方形,周长两千六百米。现存几段残垣,为高四米、宽八米左右的土墙,上上下下长着茂密的林丛。里面有的地方已经辟为粮田、菜畦,其余依然笼罩在寒烟衰草之中。传说中的屋宇、堂廨以及斩将台、练兵场等建筑和设施,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是,这并不影响它的声名远播,原因在于北宋末年徽、钦二帝曾被长期囚禁于此。
这里地形十分险要,整个宏观环境也比较特殊。牡丹江、松花江、倭肯河从西、北、东三面把它围拢起来,左右还有东山、西山为其屏障,南面却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遮拦。远远望去,人们说像个倒在地上的硕大无朋的“门”字,我仔细地端详一番,倒觉得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土囊,一个没有扎嘴儿的口袋。
一个秋天的傍晚,江面上吹过来习习的轻风,天边雾霭朦胧,半钩新月初上,除了一阵叽叽喳喳的细碎的鸟鸣,再没有其他声响。静静地,我独自站在颓残破败的城头,扫视着周遭的一切,念及八百年前的陈年旧事,心想,真是世事如棋,风云变幻,偌大的一个称雄一百六、七十年的威威赫赫的北宋王朝,竟被洪荒初辟的女真人的数千铁骑践踏在脚下,最后统通被拢进这个破破烂烂的土囊里,“收拾乾坤一袋装”了。一时百感中来,遂口占七绝一首:
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
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
生女真人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及长白山地区,开始只有十多万人,分成不相统属的七十二个部落,都在辽朝的统驭之下。到公元十一世纪末,完颜部强大起来,统一了生女真各部。这时的辽朝上层贵族日趋腐败,对生女真的压榨也更加残酷,激起了女真族人民的强烈愤恨。遂于公元1114年,在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的率领下,誓师起兵,展开了抗辽斗争。第二年,阿骨打立国称帝,建立了奴隶制的金朝。看到在金兵进攻下辽朝已岌岌可危,北宋最高统治者以为,可以通过联金灭辽,“火中取栗”,收回久被辽朝占领的燕云十六州。
本来,在女真人的心目中,堂堂的大宋天朝尽管已经武备虚弱,但是,“瘦弱的骆驼大于牛”,总还是一只余威尚在的庞然大物。可是,在联合出兵过程中,他们发现,北宋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们没有料到,那些高踞庙堂的“白蚁”,已经把这样一座摩天大厦蛀成了空壳,止消一阵卷地狂风,便可以摧枯拉朽,柱断梁颓。
于是,这头贪欲越来越强、胃口越来越大的塞外凶狮,在1125年吞噬了辽朝之后,还没来得及过细地咀嚼、消化它,便掉转矛头,兵分两路,以双钳合拢之势,朝着这个天朝“盟友”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东路由斡离不率领,从平州(今河北卢龙)直扑燕京;西路以粘罕为首,经云中(今山西大同)进袭太原,最后共同的目标是夺取北宋的都城——东京汴梁。
可是,当时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对金朝的进军企图却茫然不晓,原以为无非是掠几座城池,要两块地方,勒索一些金银财宝,到手之后就会志得意满,乖乖地撤兵。直到金兵一路上杀将过来,眼看到了黄河北岸,徽宗赵佶才慌了手脚。他想到的对策只有避战,逃逸。于是,仓皇退位,交班给他的儿子赵桓,是为钦宗;自己则做了太上皇,称为道君皇帝。名义上,说是要去安徽的亳州太清宫进香,实际上是要避地江南,逃之夭夭。他嫌汴河里行船太慢,改乘轿子,坐上轿子还是嫌慢,又换乘骡马。直到进了镇江城门,才惊魂甫定,暂时放下心来。
这面,金兵正长驱直入,逼近黄河大桥。宋军守桥部队远远望见金兵的旗帜,就急忙烧桥溃逃。而守卫在黄河南岸的两万宋军,更是连金兵的影子都未见到,就已望风遁去。当金兵用小船一批一批地从容过河之后,竟没有遇到一兵一卒进行抵抗。金军统帅斡离不慨叹道:“南朝可真称得上没有人了。假若有一两千人拦击,我们还能这样顺利地渡过天堑黄河吗?”
在兵临城下之后,北宋赖以守卫京都的大将,竟是术士郭京,是一个自称能够施行六甲神术,可以生擒金兵统帅,并且有把握击退金兵,一直赶到阴山为止的大骗子。士兵则是由郭京亲自选择的年命合于“六甲”的一些市井游民,总共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另外还有一些自称“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和“天阙大将”的人应募参加。除此之外,就是皇帝的卫士和城中的弓箭手了。钦宗天天眼巴巴地盼着这些“神兵”创造出一鸣惊人的奇迹,可是,谁晓得,这些“神兵神将”刚一出城,就被金兵打得个落花流水。郭京在城楼上眼见骗局已被戳穿,推说要亲自下去“作法”,便匆匆地带上一些残存的流氓无赖,溜之大吉。
直到这时,宋钦宗还没有从“和议”的迷梦中醒转过来,仍然委派宰相频繁往来金营,商议割地、纳币、贡献珍宝等事宜,以求得苟延残喘。在北宋朝廷接受了极为苛刻的议和条件下,金兵暂时从城内撤兵,进驻南郊的青城。而汴京城里的昏君奸相,仍然行使着他们的行政权力,一面按照金人的意旨,将城中所有的作战物资尽数集中起来,然后统统献给金人,并下令阻止各路勤王兵马开赴京师,对自动组织起来制造兵器、准备抵抗的民众进行无情的镇压;一面在最高统治层又开展了紧张的内部斗争。接受亲信的提醒和建议,钦宗赶忙派人将道君皇帝从镇江接回,以防止他在那里趁机制造分裂活动,名义上却是“奉养尽孝”。这天,钦宗到龙德宫去拜见道君皇帝,献上一杯御酒,道君一饮而尽;随手也给钦宗斟了一杯。钦宗刚要接饮,却被身后一位大臣轻轻踢了一脚。钦宗悟到这是要他防备下毒,于是,伏地恳辞,坚决不受。道君伤心得痛哭了一场。
二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开封陷落;接着,赵桓向金主上表投降。金人通过北宋文武大臣中的民族败类,将开封城内的金银、绢帛、书籍、图画、古器等物,收缴上来,劫掠一空。翌年四月初一,金人掳走徽、钦二帝和在东京的所有嫡亲皇室、宗戚,及技艺工匠、皇宫侍女、娼妓、演员等三千余人,皇室中得以脱网幸免的只有宋哲宗的废后孟氏和身任大元帅的康王赵构。金兵同时还将北宋王朝所用礼器、法物、教坊乐器和八宝、九鼎、浑天仪、铜人、天下府州县图全部携载而去。这就是旧时史书上的所谓“靖康之祸”。
说来也十分可笑,本来明明白白是两个皇帝做了俘虏,可是,朝臣奏章、史籍记载却偏要说成“二帝北狩”。其实,即便用“巡狩”字样来加以表述,也不是他们麾旄出狩,而是作为会说话的两脚动物,乖乖地成了金人的猎物了。当然,这些都是现在的话。在古时,人们已经见惯不怪,因为《春秋·公羊传》上就煌煌大书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嘛。讳什么?尊者要讳耻,亲者要讳疾,贤者要讳过。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照着这个则律记载的。
赵佶一生中最后九年的穷愁羁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站是燕山府,时在早春,有《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作。他以杏花的凋零比喻国破家亡,自己被掳北去,横遭摧残的命运,婉转而绝望地倾诉出内心无限的哀愁。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
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
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
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
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情绪低沉,音调哀伤,体现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特点。李后主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赵佶则曰:连梦也不做了,其情岂不更惨!
十月中旬,赵佶、赵桓等人,又从燕京的悯忠寺出发,被押送到旧日辽国所建中京大名城(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批被俘的北宋官员则被押往显州(今辽宁北镇县)。1128年秋,他们被押解到金国的都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金人隆重地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徽、钦二帝及其皇后都要罩头帕,着民服,外袭羊裘,其余诸王、驸马、王妃、公主、宗室妇女等一千余人,皆袒露上身,披羊裘,到金朝的祖庙行“牵羊礼”。然后,又把这两个当日的堂堂君主拉赴乾元殿,身着素服,以降虏身分跪拜胜国天子金太宗。这当然都是最为难堪的。
年末,金太宗又把赵佶、赵桓父子及皇室九百余人迁徙到韩州(今辽宁昌图县八面城),赐地十五顷,让他们种植庄稼、蔬菜,在金人武力的严密监视之下,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此前,已将当地居民全部迁出。他们原以为可以终老于此,没有料到,一年半之后,又被发配到千里之外更加荒凉的穷边绝塞——松花江畔的五国城。
这里,流传着徽、钦二帝“坐井观天”的遗闻。经人考证坐实,这个所谓的“井”,就在慈云寺西北百余米处。我在城垣内前后察看一番,确实发现了一口古井。如果属于当年旧物,我以为,也是供这些亡国贱俘饮用的水井,而根本不可能在里面住人。据分析,他们极有可能是住在北方今天还偶而可见的“地窨子”里。莫说是八百年前气温要大大低于现在,即使今天,在寒风凛冽的冬日,把两个身体孱弱的人囚禁在松花江畔的井里,恐怕过不了两天就得冻成僵尸。相反,那种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的“地窨子”,倒是冬暖夏凉,只是潮湿、气闷罢了。之所以称为“井”,无非是形容其局促、塞陷的景况。
从流传下来的赵佶的一首诗,也可以验证这种推测: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一般的井,只有盖而无门;“西风撼破扉”云云,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可见,当时绝非住在井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末代皇帝丢了江山之后,含愤自杀的寥寥可数。因为“知耻近乎勇”,若是一无廉耻,二乏勇气,就不会像明朝的朱由检那样煤山自缢,选择“殉国”一途。退而求其次,就是变装出逃。可是,出逃又谈何容易!到了穷途末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变成“率土之滨,莫非敌臣”了,往往是没有跑出多远,就被人家递解回来。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选择,索性白旗高举,肉袒出降。这在大多数亡国之君,被认为是较为理想的。他们的逻辑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新的王朝宽大为怀,只要脸皮厚一点,还有望混上个“安乐公”、“归命侯”当当,可以继续过那种安闲逸豫的日子。
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甜蜜蜜的幻想,历史上多数“降王”的日子都不好过。当了亡国贱俘以后,如果像前秦苻坚、南燕末主慕容超、大夏王朝的废主赫连昌、后主赫连定那样,很快就都死在胜利者的刀剑之下,所谓“一死无大难矣”,倒还罢了;假如类似南唐李后主和北宋徽宗、钦宗父子这样,投降之后沦为俘虏,一时半刻又能喘上几口活气,那就免不了要受到终身縻押,心灵上备受屈辱不算,身体上还得吃苦受罪,结果是“终朝以眼泪洗面”,那又有什么“生趣”之可言呢!
三
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宋太祖不问任何情由,只因“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便蛮横地灭掉南唐一样,金太宗攻占汴京,扑灭北宋,也是不讲任何情由的。而且,南唐的李后主和北宋的道君皇帝,都是诗文兼擅,艺术造诣超群,“好一个翰林学士”;却都不是当皇帝的“胚子”,他们缺乏那种雄才大略和开疆定国的本领。最后,只能令人慨叹不置:“做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巧还巧在,他们败降之后,又分别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两个同样凶狠、毒辣、残忍的对手。当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李后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料到,一百五十七年之后,他的五世嫡孙赵佶竟瘐毙在金太宗设置的穷边绝塞的囚笼之中。
说来,历史老仙翁也真会作弄人。它首先让那类才情毕具的风流种子,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的宝座,使他们阅尽人间春色,也出尽奇乖大丑,然后手掌一翻,啪地一下,再把他们从荣耀的巅峰打翻到灾难的谷底,让他们在无情的炼狱里,饱遭心灵的磨折,充分体验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
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赵佶之流的败亡,自身没有责任。恰恰相反,他们完全都是咎由自取。可以说,赵佶的可悲下场,他的大起大落,由三十三天堕入十八层地狱,受尽了屈辱,吃透了苦头,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帝鉴图说》,据说是明、清两朝皇帝幼年时的史鉴启蒙课本。其中选载了五十多个帝王的善政与恶行。在三十六件恶行里,宋徽宗自己占了三件。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信用奸人,穷奢极欲。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无道昏君,在位二十五年间,整天耽于声色狗马,吃喝玩乐,荒淫无度。凡是在这些方面能够投其所好的人,不管是朝中大臣,宫廷阉宦,还是市井无赖,他都予以信任和重用。蔡京奸贪残暴,无恶不作,却能四次入相,祖孙十一人同时担任朝廷命官。王黼多智善佞,五年为相,所蓄金帛珍宝和娇姬美妾之多,几乎能与皇帝比美。宦官童贯和梁师成,一个掌握兵权达二十年之久,成为北宋末年的最高军事统帅;一个掌管御书号令,权势熏天,连宰相都得把他当作父亲看待,因而有“隐相”之称。他们互相勾结,排斥异已,操纵了朝中的大权。而徽宗则乐得悠游岁月,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
蔡京还挖空心思,从《易经》中找寻根据,以“丰亨豫大”相标榜。说当前朝廷的宫室规模,同国家的富强、君德之隆盛不相配称,极力怂恿徽宗要“享天下之奉”,勿“徒自劳苦”。他们知道徽宗特别嗜好奇花美石、珍禽异兽,便勒令各地搜括、进献,一时间,贡奉珍品的船只在淮河、汴水中首尾相接,称为“花石纲”。当这些花石运到都城之后,蔡京又鼓动皇上兴建豪华的延福宫,分门别类放置。并用六年时间,在平地修起一座万岁山(亦名艮岳),周长十余里,高峰达九十步。山间布满了亭台楼阁,开掘了湖沼,架设了桥梁。他们确定了一条营造的标准:“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就是说,其富丽堂皇不仅达到空前,还要能够绝后。
童贯从市井中物色到一个善于饲养禽鸟的薛翁。他入园之后,便仿效皇帝出游的架势,每日集中大量车舆卫队,清街喝道,在万岁山中巡游。车上张设黄罗伞盖,并安放巨大的盘子,满盛着粱米,任凭过往的禽鸟随意啄食。飞禽饱食后便翔集于山林之中,自由来去,绝对不许捕杀。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飞禽习惯了与游人狎玩,立于伞盖之上也不再畏惧。一天,徽宗临幸万岁山,霎时,有数万只禽鸟听到清道的声音,迅速飞集过来,铺天盖地。薛翁于御前奏报:“万岁山禽鸟迎驾。”徽宗喜上眉梢,当即委之以官职,并给予厚重的赏赐。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看过一出名叫《皇帝与妓女》的新京剧。剧作家宋之的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宋人轶事汇编》和《李师师外传》,把“靖康之祸”中徽、钦二帝伙同朝中的投降派,残酷镇压主张抗金的将领和民众,甘心为侵略者效劳的种种恶行搬到了舞台上。妓女李师师和宋徽宗以及朝中几个奸臣、抗金将领吴革、代表民众的李宝等都有交往,剧情便以她为线索一步步地展开,再现了当时错综复杂、内外交织的矛盾、斗争。当然,由于戏剧本身是文学创作,有些情节出于合理想像,未必与史实尽合榫铆,但它往往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五十年过去了,剧中有些情节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脑子里:
金兵攻下开封之后,钦宗签下了降表,吴革率兵勤王自陕北前线归来。就在他节节胜利,杀得金兵马仰人翻,即将活捉敌军渠帅的关键时刻,朝廷却以“破坏和议”的罪名,要捉拿他归案。吴革“情愿做不忠之鬼,不愿做亡国之臣”,抗命杀敌,结果,却被伪装助阵、实为内奸的投降派范琼从背后施放冷箭射倒。当时,台下观众悲愤填膺,传出一片唏嘘之声。
另一件事发生在金军的囚营里。羁押中的道君皇帝,像个丑角演员似的,强装出笑脸,陪同金军将领们踢球打弹,斗鸡走狗,或者吟咏歌功颂德的诗篇,背地里却心态悲凉,愁苦万状。这一切,被天真善良的妓女——其时也遭捕入狱,陪伴歌舞的李师师偶然见到了。出于同情和信任,她便把刚刚获得的一个信息透露给他。原来,吴革在结义弟兄李宝等的悉心护理下,箭伤得到了康复,他们策划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时,趁着金人歌舞狂欢之际,带领一些勇士潜入金营,同三千在押囚犯里应外合,剌杀金军统帅,大张义旗,重整旗鼓。届时,李师师通过献歌侑酒,加以配合。
可是,李师师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无道又无良的亡国之君,竟然把她出卖了。结果,一场精心筹划的义举,最后以吴革等被捕杀、李师师当场自刎而告终。赵佶及其左右侍臣的“逻辑”是:万一举事失败,他们必然会受到牵累,到那时,想要屈辱苟活亦不可得;即使侥幸成功,最后起义军把金人赶出去,得利的也不是他这个太上皇,而是南朝的现任天子。综上分析,于是得出结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够了,无须再罗列其他了。看来,让这样一个无道昏君,在荒寒苦旅中亲身体验一番饥寒、痛苦、屈辱的非人境遇,也算得是天公地道了。
四
其实,对一般人来说,苦难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锻造人性的熔炉。一个人当缺乏悲剧体验时,其意识往往处于一种混沌、蒙昧状态,换句话说,他们与客观世界处于一种原始的统一状态,既不可能了解客观世界,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而对于赵佶之流来说,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
一则故事说,徽宗当了太上皇之后,逃避金兵,跑到镇江。这天,游览金山寺,见长江中舟船如织,因向一位禅师问讯:江上有多少只船?禅师答说,只有两只,一只是寻名的,一只是逐利的,人生无他物,名利两只船。显然其中寓有讽喻的深意。但在当时的赵佶,是无法理解的。史载,李煜在囚絷中,曾对当年错杀了两个直臣感到追悔。且不知赵佶经过苦难的磨折之后,对于自己信用奸佞、荒淫误国的行为,有没有过深刻的反思。
据传,他在五国城写过这样一首感怀抒愤之作:
杳杳神州路八千,宗祊隔绝几经年。
衰残病渴那能久,茹苦穷荒敢怨天!
古代圣人有一句很警策的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看来,岂“敢怨天”云云,倒还算得上一句老实话。
有资料记载,钦宗赵桓在流放中也填写过一首《西江月》词:
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权奸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
侵侮。 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
士忠臣何处?
词句直白、浅露,水准不高,达意而已。但是,如果真的出自赵桓之手,倒是从中可以看出,他在历经劫难之后的些微觉醒。
公元1135年4月,赵佶卒于五国城,年五十四岁。二十六年后,赵桓也在这里结束了他屈辱的一生。生前,他们都曾梦想能够生还故国。《纲鉴易知录》载,在燕山时,徽宗曾私下嘱托侍臣曹勋,要他偷逃回去转告康王赵构(即宋高宗):便可即位,救出父母。羁押中的康王夫人邢氏也曾脱下金环,使内侍交给曹勋,说:请为我向大王转达“愿如此环,得早相见”的愿望。曹勋回去以后,即向高宗奏报,应迅速招募勇士绕行海上,潜入金国的东部边境,偷偷接奉上皇从海道逃归。结果,不但意见未被采纳,曹勋本人还被放往外地,九年不得升迁。原来,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微妙、隐秘的内情。
高宗赵构乃徽宗第九子、钦宗的弟弟。公元1127年4月,徽、钦二帝被俘北去,5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后来迁都临安,建立了被称为南宋的小朝廷。他同乃父乃兄一样,也是最怕同金兵交战的。他所信用的汪伯彦、黄潜善和充当金人内奸的秦桧,都是些主张逃跑和屈膝投降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块心病,就是如果抗金成功,父亲、哥哥就会返回,那实在是难以接受的事实。明人陈鉴有诗云:
日短中原雁影分,空将环子寄曹勋。
黄龙塞上悲笳月,只隔临安一片云。
诗意是说,捎话也好,“寄环”也好,都是无济于事的,阻隔就在“临安一片云”上,当然指的是宋高宗了。
与这种委婉的批评相对照,明代文学家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则一针见血地对赵构等人的卑劣用心进行了尖锐、直白的揭露:“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清人郑板桥也写道:
丞相纷纷诏敕多,绍兴天子只酣歌。
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不过,诗中的“金人欲送”的说法并不确实。不要说活人他们不想放回,就是死者的灵柩,金人也无意遣返。徽宗已知生还无望,临终时曾遗命归葬内地,但金廷并未同意。六年后,宋、金达成和议,才答应把赵佶夫妇的梓宫送回去。至于赵桓的陵寝,由于南宋朝廷无人关心,不加闻问,所以,究竟埋在哪里已经无人知晓了。
徽宗有皇子三十一人,公主三十四人,除了赵构和早殇的以外,其他统统被俘获到穷边绝塞。在徽宗的近千名随从、钦宗的上百名随从中,有些年老体弱者抛尸于流徙途中,还有很多人惨死在金兵的剑锋之下,有一百多名“王嗣”(徽宗的后代)成为海陵王的刀下之鬼,——这是在金世宗即位诏书中罗列海陵王罪行时揭露出来的。被俘的宗亲、后妃中唯一得以生还的是徽宗的韦后、高宗的生母,在高宗千方百计的营求下,得随徽宗的灵柩返回中土。
现今五国城的东门和南门外,有许多荒丘,传说乃赵氏宗室的墓葬。另外,本世纪三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城内先后掘得许多用铁柜盛装的北宋通宝。考古学家认为,可能是金人的掳获品。在依兰一带,还流行有所谓“徽宗语”者,类似切音叶韵,传说系当时徽宗与侍从所用之隐语。
有关徽、钦二帝羁身北国的情况,宋史、金史上只是寥寥数语,《松漠纪闻》、《北狩行记》等几部个人著述,由于掌握资料有限,也都是语焉不详。诚如鲁迅先生所说,过去的历史向来都是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者如果不遭到痛骂,也要淹没无闻。就我所见的史料钩沉,要推日人园田一龟的《徽宗被俘流配记》较为详尽,但其中有些说法,还须作进一步的考证。
本来,赵佶的诗文书画都称上乘,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评说,“徽宗天才甚高,诗文而外,尤工长短句”。在书法艺术上,赵佶以其深湛的学养、悟性和独特的审美意识,跳出唐人森严的法度,选择和创造了能表现其艺术个性的“瘦金书”体。赵佶的画,同样居于北宋绘画艺术的峰巅。他从当皇帝的第二年起,便日日写生作画,长年不辍;还从宫中所存的几万件绘画作品中精选出一千五百件,反复展玩赏鉴,再从里面选出上百件,日日临习,直到每一件足以达到乱真的程度才肯罢休。他作为一个绘画大家,举凡人物、山水、花鸟、虫鱼,以及其他杂画、风俗画,各色俱备,技艺卓绝。
据说,在九年的穷愁羁旅中,他也未曾辍笔,仅诗词就写过上千首,但流传下来的极少,书画则已全部散失。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金朝初期统治者对“汉化”存有戒心,因而对流人的创作箝制极严,即使社会上偶有流传,也必然遭到禁绝;二是作者本人出于全身远祸的考虑,不得不忍痛自行销毁。赵佶谢世之前,曾遭到一子一婿以谋反罪诬告,后来事实虽然得到澄清,但釜底游鱼早已吓得惊魂四散,片纸只字再也不敢留存了。就艺术方面看,李煜要比赵佶的命运稍好一些。
五
告别了五国城,我又沿着松花江、黑龙江,一路寻访了九百年前女真部族生息繁兴、攻城略地的丛残史迹,最后来到金代前期的都城——阿城的上京会宁府,考察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龙兴故地。这座曾经煊赫百余年的王朝都会,几经兵燹劫火,风雨剥蚀,于今已片瓦无存,只余下一片残垣土阜,在斜阳下诉说着成败兴亡。
值得记述的是,据《大金国志》和《金史》记载,当时上自朝廷的宫阙、服饰,下至民风土俗,一切都是很朴陋的,充满着一种野性的勃勃生机和顽强的进取精神。可是,后来这些值得珍视的遗产,在他们的子孙身上就逐渐销蚀了。代之而起的是豪华、奢靡,玩物丧志。他们在燕京,特别是迁都汴梁之后,海陵王完颜亮之辈,骄奢淫佚,横征暴敛,简直比宋徽宗还要“宋徽宗”了。其下场之可悲,当然也和前朝一样。
汴梁城的南郊有个名叫“青城”的小镇,是当年金军受降之处,徽、钦二帝以及赵宋的后妃、皇族都曾被拘禁于此。过了一百零七年,元人灭金,亦于青城受降,并把金朝的后妃、皇族五百多人劫掳至此,并全部杀死。诗人元好问目击其事,曾写过一首七律,末后两句是:“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可谓苍凉凄苦,寄慨遥深。元好问还有一首描写元人灭金,蒙古军肆虐、掠夺的七绝:
随宫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
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它使人忆起一百多年前金兵掠宋的情景。
本来,前朝骄奢致败的教训,应该成为后世的殷鉴,起码也是一种当头棒喝。但历史实践表明,像海陵王以及金朝的末代皇帝那样重蹈覆辙,甚至变本加厉的,可说是比比皆是。时间还可以往前追溯一下。六朝时,南齐的末代昏君萧宝卷,给他所宠爱的潘妃修筑永寿殿,凿金以为莲花贴地,让潘妃走在上面,说这是“步步莲花”。不久,即为梁武帝所灭。可是,新朝并未接受前朝的教训,豪华的齐殿变作享乐的“梁台”,依旧是歌管连宵,舞彻天明。唐代诗人李商隐对此感喟无限,写下了一首有名的《齐宫词》:
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
梁台歌管三更后,犹自风摇九子铃。
看过金代的兴亡故迹,我也有无限的感喟。为此,发扬李商隐的诗意,步《土囊吟》一诗原韵,续写七绝二首:
艮岳阿房久作尘,上京宫阙属何人?
东风不醒兴亡梦,大块无言草自春。
哀悯秦人待后人,松江悲咽土囊吟。
荒淫不鉴前王耻,转眼蒙元又灭金!
唐人杜牧名篇《阿房宫赋》中,有“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警句,诗中阐发了其中的奥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