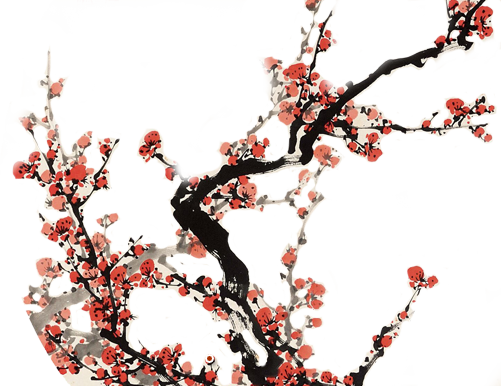关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
王充闾
一
当前,许多散文作家都在致力于提高散文的文化品位,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
我从自身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到,散文中如能恰当地融进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寻求一种面向社会、人生的意蕴深度,往往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也会使单调的丛残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
三年前,我曾有中州之行,访问了三座历史名都,回来后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组题为《面对历史的苍茫》的散文。开封、洛阳和邯郸,这些曾经繁华绮丽的历史名都,历经世事沧桑,许多当年的胜景已经荡然无存,但在故都遗址上,却有沉甸甸的文化积存在那里。漫步其间,我脑子里涌现出很多诗文经史,翻腾着春秋战国以来几乎整部的中华文明史的烟云。这些散文,没有停留于记叙曾经发生过的史事(尽管这也是颇有教益的),而是在解读历史的同时,着意揭示作者对于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
“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三百多年的宋王朝留在故都开封的是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更是一面文化的回音壁,是诗人们从中打捞出来的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是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探寻。
邯郸古道上,既有燕赵悲歌,也有黄粱美梦,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意旨,竟能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和谐地汇聚在一起,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悠远的中国文化深入探究的兴趣。
在凭吊洛阳魏晋故城遗址后写成的《诗文的代价》中,我没有重复《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语,而是通过写废墟――悲剧的文化,展现搏斗后的虚无,成功后的泯灭,着眼点在于阐释文学的代价。清人赵翼有两句著名的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说的就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总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魏晋时期留给后人可供咀嚼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思想十分活跃。部分文学家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敢于荡检逾闲,抒发真情实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
尤其是魏晋时期文人以艺术风度所造就的诗性人生,给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适,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于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他们的诗酒生涯,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人们一般的印象,文明之花盛开于中土,古代蛮荒塞外的历史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并非如此。从公元前几世纪的西周开始,生长在北方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就拨开洪荒的流云,燃起文明的爝火,相继跨上奔腾的骏马,闯入了历史的疆场。他们的铁骑越过万古荒原,越过长城、黄河,踏上中原大地,以其沉雄的呐喊与滴血的泣诉,共同叙述着那从梦幻走向现实的艰难历程,叙述着历史的无奈与无情;更以其蓬勃的朝气,锐不可当的攻势,给予每个从励精图治到骄奢怠惰的中原王朝以致命的冲击。而每一回合的搏斗,都昭示着中华民族从分裂、对抗走向统一与融合的历史时空,装订着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苦难与辉煌。
带着探求这类社会文明继承、发展规律的渴望,我访问了女真族的策源地三江平原和金代的早期都城阿城,撰写了文化历史散文《土囊吟》与《文明的征服》。女真族原是十分落后的,立国当时,尚无文字。但是,他们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铁蹄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超过自己数十倍的强大军事对手,先后灭辽蚀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俘获到五国城下。与此同时,他们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蒙元、满清一样,当从塞北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演进、发展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动机、目的相背反。
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他们在充分享用“全盘汉化”的文明硕果的同时,也在丧失一些本民族固有的优势。从茫茫塞野的“弓刀夜雪三千骑”到繁华都市的“灯火春风十万家”,对于一个世世代代生长在艰苦环境中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场十分严峻的生命与生存的挑战。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二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我们从辛弃疾的词里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大凡人们普遍向往的名城胜迹,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文人骚客留下较多屐痕、墨痕的所在。他们凭着对大自然的特殊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诗文,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数不尽的画一般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象。他们登临远目,抚今追昔,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限制,泯除种种界隔,化解由岁月迁流所引起的怆然寥落之情、无常幻灭之感,直接与古今情事取得沟通。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当然,人们在欣赏自然风物的同时,也是在从中寻找、发现和寄托着自己。
而那些遍布于名城胜迹,见诸方志,传于史简的诗文和轶闻、佳话,既为你展开垂天的羽翼去联想与发挥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又使你不期然而然地负上一笔情思的宿债,急切地渴望着对其中实境的探访,情怀的热切有时竟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这样,即使是首途,是乍到,也都如游旧地,如晤故人,彷佛踏进了重重梦境,返回了精神家园。此刻,那些名章妙句、鲜活形象,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尘封已久的记忆被拂去了时间的尘埃,一个个都涌动起来。它们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通过它们的参与,使历史意识和人生感悟汩汩流出,从一个景点、一桩事件走入历史的沧桑。你会觉得人文、历史、自然浑然聚合在一起,启动着内心的激情与联想。
也正因为这样,一些作家总习惯于凭借自己的游踪,对一些名城胜迹作历史的考察与观照,对社会、人生作哲学性的反思和叩问。他们不肯停留于一般的纪游、写景、述感、抒怀,只写耳目所及的事物,只写一个横断面,而是追求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既写现在,又写过去,既写现实的发展,又写历史的变迁。他们喜欢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的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努力反映出历史、时代所固有的那种纵深感、凝重感、沧桑感。他们喜欢结合现实风物的描述,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去观照、思考和发掘已知的史料,给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生活以新的认识、新的诠释,体现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的感悟,从而使作品获得比较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同时,也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的杠杆,让自己的灵魂在历史文化中撞击,展开深沉的人文批判,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因此,当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观赏现实的景物,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有厚度的艺术世界。如同诵读着古人的诗书,倾听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回音壁,通过一块情感的透镜去观察历史,从而获得了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采的效果。那民族兴衰、人事嬗变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留痕,人格的悲喜剧在时间长河中所显示的超出个体生命的意义,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不倦探寻,以及在终极毁灭中所获得的怆然之情和宇宙永恒感,都在新的境遇中展开,给了我们远远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
这是诗章,也是历史,更是哲学,是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远者如近,古者如今,活转来的经史诗文给了我们“当下”一个时空的定位,更给我们一个打开的不再遮蔽的视界。
在这里,我们与传统相遭遇,又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它,于是,历史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是为我们思考“当下”、思考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此刻,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会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这种情志,包括了对古人的景仰、评骘、惋惜与悲歌,闪动着先哲的魂魄,贯穿着历史的神经和华夏文明的汩汩血脉。
在这里,人们既从历史老人手中接受一种永恒悲剧的感怀,今古同抱千秋之憾,与山川景物同其罔极;同时,又在自然空间那里,获取一种无限的背景和适意发展的可能性,感悟到,人不仅由自然造成,也由自己造成;不仅要服从自然规律,也能利用自然规律;人死后复归于自然,又时刻努力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
数千年来,人类执拗地寻求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本体,不过是为了摆脱自我的局限,走出自己立足的那个有限的时空交叉点。历史与文学是人类的记忆,又是现实人生具有超越意义的幻想的起点。只有在那里,人类才有了漫长的存活经历,逝去的事件才能在回忆中获得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成为我们当代人起锚的港湾。
历史的脚步永不停歇,每日每时都迎来无量数的新事物,又把种种旧的事端沉埋下去。翻开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会看到,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曾付出难以计数的惨重的代价。不要说汲取它的全部教益,即使是百一、千一、万一,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也将是受惠无穷的。因此,聪明的人总要努力战胜对于历史的多忘症,使前事不忘,成为后事之师。
我们应该承认,历史过程本身和对历史过程的记述、对历史的解释是两个层面。历史本体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的史学家说,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忆”它,给它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这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历史作为过去发生过的事,事实上存在过,与史家或什么人的回忆与否无关,即使无人回忆它,它也是存在过。而作为史学,则必然跃动着史家灵魂的轨迹,人们无法拒绝对于历史的当代阐释。在记述与解释历史过程中,难免带上记述主体、研究主体的剪裁、选择、判断、描绘的痕迹。
而且,就历史本身来说,由于诸多条件的制约,历代失记和被遗忘的,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看,都要大大超出已记的部分。就已记的部分来说,人类本身有外在与内在之别,历史所记载的,或者说后人所面对的,多数属于外在的东西;而内在的东西已随当事者的消逝而永远不可能再现。后人只有凭借这些外在的东
西传递的信号,试图为历史“黑箱”中的一个个疑团解秘。
因此,早在九百年前,王安石在《读史》诗中就曾慨叹:“自古功名多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 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毛泽东在《读史》词中,也曾慨乎其言地发问:“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
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
可见,面对历史的苍茫,发微探赜,鉴往知来,谈何容易!但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散文作家,又必须直面这一课题,作出相应的答案。
三
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凡是伟大的作家,都具备很强的历史选择能力、判断能力、结构能力和想象能力。既写历史的崇高、壮烈,又写历史的沉重与苍凉;既写创造的伟力与成功,也写世事的沧桑与人生的悲剧意识。诚然,历史留存着人类以往一切活动与成就的纪录,使它们不致因时空条件的限制而趋于消逝;但是,时空的限界毕竟又造成所有个体生命的割断、隔绝与消逝,迫使人们的情志需求有很大一部分归于落空,也使人类在宇宙中自觉的地位与作用受到局限与压缩,因此,时空条件本身,就足以给人一分难喻的怆怀。
当然,对此,伟大的作家并不是无为与无奈的。他们总是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发扬与重铸,或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对文化生命作真正的慧命相接,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去体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后的欢愉;或关注历史上递嬗兴亡、人事变迁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意义,强调人情物事的文化价值,而使某些特殊人格与精神的象征挺立于时间长河之中,显示出一种宇宙的乐感与恒定感;或是夸张时间的消蚀力,以致一切人事作为都隐现了终极毁灭的倾向,如此而引发一种宇宙的悲剧性与无常感。
文学从来就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文学家与史学家都是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的,都是通过搜索历史与现实在心中碰撞的回声,表现他们对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因此,它们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上,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就是说,实现史学与文学在现实床笫上的拥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现在,有些史学研究较为严重地存在着忽视审美价值的追求的倾向,引不起读者的阅读欲望与审美期待。通过文史联姻,可以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欢快、生机与美感,带来想象力与激情;而史眼、哲思的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又能使文学倩女变得深沉、凝重,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沧桑感,体现出哲学意境、文化积累和心灵的撞击力,引发人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一些悲剧因素,更能使读者对往事的留连变成深沉的追寻,在对历史的勘劾中也多了一层苍凉。“若是杜陵无史笔,姓名恐亦少人知。”诗人吴静在这里说的是,史笔在诗词创作中断不可少,对于散文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创作这类散文,形象地说,作家是一只脚站在往事如烟的历史埃尘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这种与历史的交谈,其宗旨不应是简单地再现过去,而是从对过去的追忆、阐释中揭示它对现在的影响和历史的内在意义。应体现作家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对历史的创造性思考与沟通,从而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价值参照。要能反映出作家深沉的历史感,进而引发读者的诸多联想。
同样,在阅读这类文化散文过程中,读者也是从现在的语境去理解过去,从读者自身文化的参照系或“前理解”出发去把握过去,而且,把自己所处时代的期待视野或“前理解”带入文本的阅读之中,渗透进新的历史意识。
这种文化散文同一般的史学研究著作的区别,除了文体上的自然属性的差异,至少还应有以下三点:
一是它体现了作家强烈的主观感受,这一点与咏史诗有些相似。“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杜牧咏赤壁之战的名句;还有白居易咏曹操的诗句:“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没有太大的价值。可是,在诗人的笔下,却常常作各种主观猜想,以收“八面受敌”,纵横剖断之效。
如果说,史学是史家心灵的历史,史家应有自主的人格,坚持个性化的独立的批判精神;那么,历史文化散文作家就更应高扬主体意识,让自我充分渗入对象领域。实际上,在阐释历史的过程中,作家本人也在被阐释――读者通过作品中的独特感悟解读了、发现了阐释者。在这里,最关紧要的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要在对历史的观察中,凝注创作主体敏锐的目光,看到他人所没看到的东西。历史文化散文中对象的描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作家的自我期待和价值判断,折射着作家自我需求的一种满足。因此说,创作历史文化散文,首要的忌讳是丧失自我。
二是它洋溢着作家灵魂跃动的真情。既是散文,总离不开抒情。真情是文学艺术、也是史笔的灵根。它不仅仅满足于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还具有诗一般的激情和深沉的美感。它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使文章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力求在情感和理智两方面感染读者,征服读者。
三是它闪现着理性的光辉。历史就是人生,人生必有思索,必有感悟。缺乏深沉的历史感,就无所谓深刻,也无法撄攫人心。因此,在散文作家的笔下,向来都是思想大于史料的。
这类散文中的思想与情感,一如历史老人本身,是深沉的、恒久的积蓄的自然流溢。它既不同于诗歌中的激情迸射,论说中的踔厉风发;也不是少男少女般的情怀的直露与挥洒。情与理,相生相克,有个如何统一的问题。我想,它们应是弥散式、复合式的交融,而不能是各张旗鼓,互分畛域。
说到文史联姻,学术界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影响作品的科学性。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文胜质则史”(文采多于朴实,则未免虚浮)。从今天来看,这种担忧也不是无谓的,有些作品确实存在着这个偏向。其实,科学性的丧失,并非由于强调了文采。本来,“文史不分家”是我们固有的优秀传统,只是,后来逐渐地丢失了。司马迁的《项羽本纪》、翦伯赞的《内蒙访古》、茨威格的《滑铁卢的一分钟》,都是“文质彬彬”,“焕乎其为文章”,达到了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并没有因其文采斑斓,而丧失了科学性。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历史的客观性,而不在于表现手法。
当然,写作历史题材的游记散文,既要把历史收在笔下,把读自然、读诗、读史融为一体,又不能为历史所累。史学与文学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个是“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壮士干戈”;一个是“醉失桃源,梦回蓬岛,满身风露”。一个是把激情隐在冷峻的后面,要述往事思来者,探因果求规律;一个是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探索艺术的弹性“空筐”。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风光胜迹,同时又记索古人的名篇佳什的时候,对书卷与历史的多情,往往会加重情怀的负累。这时,设法走出古人,摆脱局限,找出一片“阶前盈尺之地”来创出自己的辉煌,就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