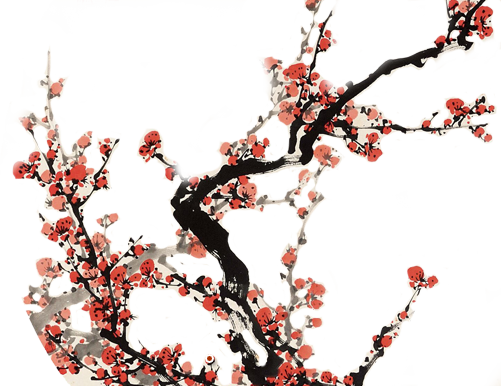王充闾
一
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是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散文必须真实,这是散文的本质性特征,一向被我们奉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艺术,惟其是艺术,作者构思时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和张开想像的翅膀;必然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作必要的艺术加工。两者似乎存在着矛盾。尤其是,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当历史成其为历史,它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像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因此,海德格尔说,历史的真意应是对“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其实就是一种文本化,其间必然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
很难设想文学作品没有细节描写,因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与个性。《史记》中写汉初名相“万石君”石奋一门恭谨,就采用了大量细节。石奋的长子石建谨小慎微,有一次书写奏章,皇帝已经批回来了,可是,他还要反复检视,终于发现“马”字有误:这个字四点为四足,加上下曲的一笔马尾,应当是五笔,现在少写了一笔。他惊慌失措,唯恐皇帝发现了怪罪下来。石奋的少子石庆,一次驾车出行,皇帝在车上问有几匹马拉车,他原本很清楚,但还是用马鞭子一一数过,然后举起手说:“六匹。”小心翼翼,跃然纸上。太史公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当时官场中那种终日战战兢兢、恭谨自保的政治风气。
明代思想家李贽讲到艺术创造时,说一个是“画”,另一个是“化”。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这就触及到散文写作中想像与虚构这一颇富争议的话题。近年来,随着新生代作者的闯入,小说家、学者的加盟,以及跨文体写作的出现,散文创作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特别是作家的主体意识在不断增强,已不满足于传统散文单一的叙述方式,而是大胆引进西方的多种表现手法,吸收其他文学门类的写作特点,辅之以象征、隐喻、虚拟、通感、意象组合等艺术手法,意识流动,虚实相间,时空切换,场景重叠,使散文向现代性、开放性拓展。
事实上,早在“散文的想像与虚构”成为问题之前,有些作家已经在悄悄地进行着大胆尝试了。出现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散文家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是一篇优秀的散文作品,曾经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可是,许多人都知道,它却是经过想像与虚构,对真人实事进行大胆加工的产物。1956年上海合唱团招考新团员,一名女青年报考,由于考试前夕她在杨树浦参加一场救火,弄倒了嗓子,以致影响了考试成绩,但合唱团还是破格录取了她。何为当时正在医院休养,听家人讲述了这件事,便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设计出第二次考试的情节,加进了苏林教授这个关键性人物,改换了女主人公的名字;文中陈伊玲身着“嫩绿色的绒线上衣,一条贴身的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实际也并非如此,是作者为了加强形象的感染效果,从所住医院一位实习医生那里移植过来的。
这个典型事例说明了,生活的真实是基础,艺术的真实是手段。前提是散文是艺术,而且是一种侧重于心灵表达的艺术。黑格尔指出:“艺术作品既然是由心灵产生出来的,它就需要一种主体的创造活动,它就是这种创造活动的产品;作为这种产品,它是为旁人的,为听众的观照和感受的。这种创造活动就是艺术家的想像。” “在这种使理性内容和现实形象互相渗透融会的过程中,艺术家一方面要求助于觉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还要求助于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气的感情。”
二
今年三月中旬,我率领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到日月潭观光,接待我们的是南投县文化局长,他是一位文学博士。在同我们交谈时,他直率地说,总觉得作家们想像力不足,有时过于拘谨。他说,有一次访问日本,见到了杨贵妃的墓,便问有关人士“根据何在”。答复是:“你们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写得很清楚嘛!”博士反诘:“杨贵妃不是死在马嵬坡吗?《长恨歌》里分明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答复是:“《长恨歌》里还讲:‘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海上仙山在哪里?就是日本嘛!”博士说:“这种颠倒迷离的仙境,原都出自当事人与诗人的想像。”答复是:“什么不是想像?‘君王掩面’,死的是丫环还是贵妃,谁也没有看清楚;所以才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就这样,生生造出一个“贵妃墓”来,结果还振振有辞!
历史散文创作讲求真实,关于史事的来龙去脉、真实场景,包括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行为,都应该据实描绘,不可臆造;可是,实际上却难以做到。国外“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与历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脱离不了文本性,历史文本乃是文学仿制品”,“历史还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种虚拟”的论点,我们且不去说;这里只就史书之撰作实践而言。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原来,“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孟轲读过上古时的典章文献汇编《尚书》中关于“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的记载,就曾提出过疑问,从而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尽信书,不如无书。”到了宋代,当学生问到“《左传》可信否”时,著名理学家程颐的回答是:“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我们再来看被奉为信史和古代散文典范的《史记》。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详细记录了鸿门宴的座次,说是项羽和他的叔叔项伯坐在西面,刘邦坐在南面,张良坐在东面,范增坐在北面。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交代?因为有范增向项羽递眼色、举玉玦,示意要杀掉刘邦的情节,他们应该靠得很近;还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项伯用自己的身体掩蔽刘邦,如果他们离得很远,就无法办到了。司马迁写作《项羽本纪》大约在公元前94、95年前后,而鸿门宴发生在公元前206年,相距一百一十多年,当时既没有录相设备,而战争年代也不大可能有关于会谈纪要之类的实录,即使有,也不会记载座次。那么,他何所据而写呢?显然靠的是想像。
三
中国文学史上还有一个典型事例。《古文观止》中有一篇《象祠记》,作者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当时,贵州灵博山有一座年代久远的象祠,是祀奉古代圣贤舜帝的弟弟象侯的。当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诚地祀奉着。这次应民众的请求,宣慰使重修了象祠,并请流放到这里的王阳明写一篇祠记。对于这位文学大家来说,写一篇祠记,确是立马可就;可是,他却大费踌躇了。原来,据《史记》记载,象为人狂傲骄纵,有恶行种种,他老是想谋害哥哥舜,舜却始终以善意相待。现在,要为象来写祠记,实在难以落笔:歌颂他吧,等于扬恶抑善,会产生负面效应;若是一口回绝,或者据史直书,又不利于民族团结。反复思考之后,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判断象的一生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段是个恶人,而后段由于哥哥舜的教诲、感化,使其在封地成为泽被生民的贤者,因此死后,当地民众缅怀遗泽,建祠供奉。《象祠记》就是这样写成的。其中显然有想像成分,但又不是凭空虚构。因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爱弟弥谨”,“封帝象为诸侯”的记载。据此,作者加以想像、推理,既生面别开,又入情入理。用心可谓良苦。
这在西方也早有先例。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占有四分之一篇幅。修氏自己承认:“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辞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接近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说:“我以为一种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这话不假。我们都看过《罗生门》这部影片,对于事件的真相,在场亲历者言人人殊。所以,有人说,“史,就是人们口上的一撇一捺。”看来,坚持历史事件包括细节的绝对真实,“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当然,这种想像必须是有限制的,要在尊重客观真实和散文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真人真事或基本事件进行经验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艺术加工,必须避免小说化的“无限虚构”或“自由虚构”;特别是有些散文种类是不能虚构的,比如,关于现实中的亲人、友人、名人的传记以及回忆性、纪念性文章,都是写作者同时代的亲历亲见亲闻的事,与事涉远古或万里悬隔迥然不同,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绝不应随意地想像、虚构。须知,这类散文美学效果的实现,是借助于其内容或主体的丰富而特殊的客观意蕴,真实与否,影响是至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