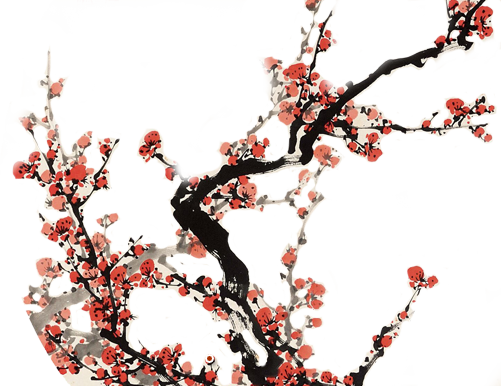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陈桥崖海须臾事
一
我喜欢旅游,更喜欢在足迹所至的山川灵境中寻觅文学的根、诗性的美,体味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的至深的理,追摹一种光明鲜洁、超然玄远的意象。
而脑子里由于积淀着丰富的“内存”,每接触到一处名城胜迹,都会有相应的诗古文辞、清词丽句闪现出来,任我去联想、品味。我也习惯于从那些诗文中发掘着沉甸甸的记忆,演绎其间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追寻那种“事外有远致”的神韵。于是,历史的神经与血脉,生命的欢愉与悲戚,在这里就赋有了诗性,赋有了超越时空的魅力。
也可以说,这些诗古文辞使我背上了一笔相当沉重的情思的宿债,每时每刻都急切地渴望着对于诗文中的实境的探访。那种情怀的热切,大概不亚于思念故乡、怀想亲友、眷恋情人,有时竟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
这次我踏上中州大地,同样是被一些古代诗文典籍牵引着。记忆中,前人何希齐有这样两句诗:
陈桥崖海须臾事,
天淡云闲今古同。
正是它,把我引到了开封东北四十五华里的陈桥驿。
这是一个普通至极的北方小镇。低平的房舍,窄狭的街道,到处都有人群往来,却也谈不上熙熙攘攘。只是由于一千多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兵变”,导致了王朝递嬗,便被载入了千秋史册,而成为中华名镇之一。
唐朝末年,群雄混战,藩镇割据,形成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后来成为宋朝开国皇帝的赵匡胤,当时不过是一个中层将领。由于跟随后周世宗柴荣作战有功,被提升为殿前都点检,统领精锐的禁军,担负着防守京师汴梁的重任。这样,他就开始确立了在禁军中的统帅权威,有意识地培植了自己的势力,暗地里同其他禁军将领石守信等结拜为“十兄弟”。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死去,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是为恭帝,由他的母亲符太后掌握政权。翌年元旦,河北镇州、定州谎报辽朝和北汉联兵南下,向后周进攻。慌急中,符太后和宰相范质等未辨真假,便派遣赵匡胤率领禁军出城迎战。赵匡胤的军队刚刚出动,汴京城内便传播起“点检做天子”的舆论。
正月初三晚上,大军行至陈桥驿宿营,军帐设在东岳庙。深夜,军中部将在赵匡胤的胞弟赵光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的策动下,集结于军帐之外,声言要拥立赵匡胤为皇帝。赵匡胤装作酒醉未醒,慢腾腾地起床坐帐,将士立即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的身上,然后一齐跪拜,高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现在,陈桥驿还保留着关于这次事件的许多文物,主要有当年设过军帐的东岳庙,赵匡胤拴过战马的系马槐,众将领饮过水的古井和几处大小碑刻等。东岳庙创建于五代时期,为中州大地上的著名古迹。千余年来,几经修缮,现在,大殿已辟作展览室,介绍陈桥兵变的经过。几块石碑上分别刻着清人顾贞观、张德纯和金梦麟等人即兴咏怀的诗词。
漫步古镇街头,玩味何希齐诗中的意蕴,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的确,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末帝赵 在蒙元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今都未曾发生什么变化。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让人们生发出许多感慨。不仅接触到古人“通天尽人”的怆然感怀,体味到哲人智者的神思遐想,而且,为研究史事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提供了足够的思考空间。有人评说,何希齐诗中的寥寥十四个字抵得上一部《南华经》,自是夸张之言。但诗人“纳须弥于芥子”,以少胜多、举重若轻的涵盖力,实在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想像的空间。
二
古往今来,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交叉点上,无论人们怎样冀求长久,渴望永恒,但相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却只能是电光石火一般的瞬息、须臾。生命的暂住性,事物的有限性,往往使人堕入一种莫名的失望和悲凉。但这又是难免的,因为只要生活在具体的时空里,每一个个体的人与事,就难免显现出它真正的渺小和空幻。为了摆脱这一根本的局限性,超出生命长度,得到更多更多,无数英雄豪杰费煞移山气力,耗尽无涯岁月,到头来总不能如愿以偿,最后只好望望然而去。大约只有在宗教和艺术的幻想中,才可能侈谈所谓“绝对的超越”。一切历史只能复活在回忆之中,一切“绝对的超越”,一切永恒,只能存在于想望之中。
人生的历程是不可逆转的。任何人生命的时空,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一次性的。正是这生命的一次性,使我们从出生的一刻起,就面临着死亡,面临着结束。因此,作为个体的生命,暂居性便成了我们无可改变的状态。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所能亲历的只是时间中的瞬间。盖世英杰也好,村野凡夫也好,无论是谁,分享的都只是这个永恒世界中的短暂的现在。还是李太白说得透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晚年写过一部《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上起鸿蒙初辟之时,下至元代,共分十部分。其中第三段的开场词,是一首《临江仙》,上阕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
旧在,几度夕阳红。
无非是览史兴怀,抒写由沧桑迭变所引发的人生感慨。这里化用苏轼《赤壁怀古》的成句,巧妙地把长江东逝与人物迁流联系起来。江水滔滔,今古无异,而历史上匆匆来去的“千古风流人物”,却如巨浪淘沙,消逝净尽。
诗人纵观历史,思量世事,发现了一个令人嗒然无奈的事实:“是非成败转头空”。万千成败是非,转瞬间烟消云散,与历史长河相比,实在显得非常的渺小与短暂。杨升庵对历代盛衰兴亡、千古英雄成败的彻悟,与诗人何希齐的充满哲理性的感慨,可谓异曲同工。当然,他并不是无谓而发的,里面渗透着他从自身的颠折遭际中所获得的真切、实际的教训。
杨升庵出身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四川新都的一个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父亲杨廷和为内阁大学士,一朝宰辅,元老重臣,而祖父、叔叔、弟弟、儿子,也都是进士及第,因此,有“一门科第甲全川”之誉。他自己二十四岁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和经筵讲官达十二年之久。早期的仕途上,飞黄腾达,春风得意。
后来,明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遵照《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之义,明世宗以同辈庶兄弟的身份继统,于是,发生了承认皇统还是尊奉家系的所谓“大礼之议”的激烈论争。杨升庵与皇帝意见针锋相对,坚定地站在当时担任宰相的父亲一边,极力主张承认皇统,要皇帝以武宗之父孝宗为父考,而称其生父兴献王为叔父。当时,杨升庵心骄气盛,放言无忌,而且,事后又纠集一些同僚撼门恸哭,因而重重地触怒了世宗皇帝。在两遭杖刑,死而复苏之后,被远谪云南永昌卫三十余年。转瞬间就结束了仕宦生涯,由权力的峰巅跌入幽暗的谷底。这种政治上的起落颠覆,对他的打击无疑是极大的。
但是,作为一代哲人,他从庄子那里悟解了达生之道,认识到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尽可奉行“模糊哲学”,等同地看待那些荣辱、穷通,是非、得失。只要自己能够克服心理上的诸般障碍,则对人间万事尽可以弛张莫拘,舒卷无碍。恰如他在《临江仙》词的下阕中说的: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
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不要说后世的论者,即使他自己,数十年后,作为一个远戍蛮荒的平头百姓,徜徉于山坳水曲之间,以淡泊的心境回思往事,料也能够感到,当年拚死相争的所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皇上称父亲为皇考还是为皇叔的“大礼”,不过是“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真个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
可以说,这首词既是他多年谪戍生涯的真实写照,刻画出他以秋月春风为伴,寄情渔樵江渚的闲情逸趣,也是诗人赖以求得自我解脱,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又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正是这种超然物外,摒弃种种世俗烦恼,对个人的一切遭际表现出旷怀达观的人生态度,帮助他渡过了漫长、凄苦的谪戍生涯,最后得以古稀上寿,终其天年。
而且,由于他投荒多暇,于书无所不读,著述之富称为明代第一,在哲学、文学、史学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失败促成了他的成功。他在仕途上的惨痛失败,为他在学术、创作上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他在物质生活上的损耗,恰恰增益了他在精神世界中的获取,他以摒弃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为代价,博取了传之久远的学术地位。
可是,正如古人所慨叹的:“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
三
在陈桥驿,信步徜徉,我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位“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纵横捭阖,睥睨一世的旷代枭雄赵匡胤。他在自立为帝以后,十七年间,主要开创了两个方面的事业:对外削平南方一些割据政权,对内加强中央集权,铲除藩镇势力。两者的目的却是一个:保证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万世一系。为此,可说是虑远谋深,不遗余力。
宋太祖受禅即位,南唐国主李煜是唯一前来朝贺的君主。尔后,南唐一直以附属国的身份称臣纳贡,从无异志,后来甚至主动撤去国号,自称“江南国主”,进一步表示臣服。李煜本人由于酷信浮图,留意声色,属文工画,无心振兴国家、强兵修武,可以说,对大宋江山构不成任何威胁。
但是,即使这样,宋太祖也不想放过他。为了制造进攻南唐的借口,便指令李煜亲自到京城朝拜。南唐一些大臣认为,李煜此去定被扣留,因此力加劝阻。这样,正好堕入太祖预设的彀中。于是,以南唐有意“抗旨”为由,堂堂正正地派出十万大军进击。李煜急忙派遣能言善辩的徐铉,前往汴京面圣,请求退兵。诉说南唐对大宋天朝一向百依百顺,没有任何得罪之处,现在,大兵压境,似乎师出无名。宋太祖赫然震怒,不加任何掩饰地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耶!”是的,“匹夫无罪,获璧其罪。”狼要吃羊,难道还要说出什么理由吗?
一天,太祖向谋臣赵普提出了两个问题:唐末以来,数十年间,为什么走马灯似
地换了八姓十三个君主,争战无休无止?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此息天下之兵、建长久之业?这里充分反映出赵匡胤积怀已久的心迹。应该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虑如何避免宋王朝继五代之后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如何永保赵氏家族万世一系的问题。
赵普的答复是:问题的核心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太祖又问:那么,有何根治的
办法?答曰:只有夺他们的权,收他们的兵,控制他们的钱谷。这样,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了。宋太祖连声说,我懂了,我全明白了。原来,君臣二人的想法完全一致。
宋太祖从自己据有天下的事实,看到手握重兵的人的极端可怕。就是说,异已的军事力量,可以对政治起支配作用,是对既得政权的最大威胁。因此,对于身边一些共同举事的军界首脑,产生了强烈的疑忌心理,不能不时刻加以防范。于是,趁慕容延钊与韩令坤二人出外巡边、回京朝见的机会,首先解除了他们禁军主帅的兵权,安排到外地当节度使;并且,此后不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
而禁军将领石守信等有拥立之功,不好下令罢免,便实行了第二步棋:四个月后,利用晚朝机会,请这些禁军宿将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屏退左右侍从,太祖显得十分亲热地说:如果没有众卿的拥戴,我是不会有今天的。然而,众卿又怎能知道,做皇帝也实在是太艰难了,远远赶不上做个节度使那样舒服,一天到晚都不能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听了,赶忙叩问缘由。他便接上说:我是担心天下坐不安稳啊。皇帝的位置,人们都争着坐。虽然你们没有异心,然而部下总是希图富贵,一旦有人也以黄袍加身,你们想要不干,能办得到吗?
一席绵里藏针的话语,使这些将领觉察到自己已经深受疑忌,弄得不好将要遭致杀身之祸。于是,纷纷泣谢叩头,要求太祖指出一条“可生之途”。宋太祖就势开导说,人生一世,犹如白驹过隙,所以那些期望富贵的人,都想广积货财,多享快乐,使子孙免受困乏,常保康宁。你们这一辈子也够辛苦的了,不如交出兵权,前去地方任职,多买些良田美宅、歌姬舞女,日夕欢宴,以乐天年。我还要同众卿结为姻亲,君臣之间永无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美好吗?
大家见皇上说得如此直白,便连连谢恩。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都上表称病,请求免去掌管禁军的职务,到地方当节度使,太祖欣然同意。事后,为了兑现酒席上的承诺,安抚这些失去兵权的禁军统帅,太祖也真的将一妹二女同他们结了姻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三
在解除武将兵权的同时,宋太祖又起用一批文臣担任知州职务,并在各州设置通判,使其权力与知州相等,以分散地方长官权限,避免出现个人专权的弊端。地方上的军事、民政、财赋、司法权限,全部收归中央管辖。在中央,对宰相实行分化事权,相互制约的办法,把军事行政权分出,划给枢密院;国家财政和地方贡赋划给三司。这样,宰相便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执政的群体,包括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三司使等十来个人。任何一个相职都不能独断军政大事,最后全都听命于皇帝。
对军队更是严加控制。军权一分为三,“三衙”负责日常管理、训练,枢密院负责调动、发兵,最高指挥权归于皇帝。禁军之外,还有厢军,其中精锐部分,全部收入禁军,厢军不再参加训练,就根本不具备战斗力了。针对这一举措,司马光评论说,这样一来,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虚弱,远不是京师的对手,自然谁也不敢再有异心,只能服服帖帖,惟命是从。
为了防止将领出外作战不受君命约束的情况发生,宋太宗更进一步实行“将从中御”的对策,每次出征,皇帝都要亲授事先拟好的“阵图”,大自战略布局,小至部伍行止,都不得擅自改变;同时,派遣宦官监军。结果,就像叶适所言:“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宋初立国伊始,即大力提倡封建道德,崇尚礼义,声称“以孝治天下”,把孝经列为群经之首,作为宗室子弟和民众的必读书,目的在于杜绝犯上作乱。注重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宋朝统治者之所以猛烈抨击唐太宗“杀兄篡位”,骂他“为子不孝,为弟不悌,悖天理,灭人伦”,也无非是为了防止“玄武门之变”重演。有人也许会问:那么,赵匡胤为什么不提倡“忠君报国”呢?道理很简单,他自己得天下的路子就不正,若是强调“忠君”,他总觉得有些嘴短。
为了赵氏王朝的万世一系,赵匡胤、赵光义,这对开基创业的难兄难弟,真可谓呕心沥血,“机关算尽”。可是,历史的发展常常是动机与效果大相迳庭,许多事情都不是始料所及的。秦始皇惟恐诗书乱政,儒生造反,实行焚书坑儒、毁灭文化的绝招,可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晚年,太史占卜,谓“女主当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于是,太宗对疑似的人严加查治。默想武卫将军李君羡,小字五娘,且他著籍武安,又封为武连县公,处处带着“武”字,莫非应在此人身上?遂调他出外,任为华州剌史,后有御史弹劾他谋为不轨,干脆下诏活活处死。可是,太宗竟没有想到,娇滴滴的武媚娘就在身旁,最后还是“祸起萧墙”。
宋太祖同样也没有料到,像当年后周的符太后领着刚刚七岁的周恭帝仓皇辞位一样,三百多年以后,赵氏王朝的寡妇孤儿——谢太后和恰好也是七岁的宋恭宗,不得不逊位于元世祖忽必烈,亦步亦趋地重复了前朝亡国败降的命运。元代诗人有这样两首七绝:
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旌旗。
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刘因:《书事》
忆昔陈桥兵变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
——北客:《宋太祖》
诗出两人之手,内容却不谋而合,都是讥刺宋太祖赵匡胤的。元将伯颜也曾对南宋的降臣说:“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历史上的惊人的相似之处,确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四
走进原为北宋都城汴梁的开封市区,空间没有跨出多远,时间却仿佛越过了千年,真有那种“一步走进历史,转眼似成古人”的感觉。历史风烟在胸中掠过,那沉埋于地下的万种喧嚣与百代繁华,已经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而生者自生,死者自死,人生舞台上还在上演着各色的悲喜剧,生命也就同时间一样,在文字传承和现实记忆中彼此衔接着,而成为一页页的历史。
整个古城,简直就是一座充满历史回声的博物馆,古色古香,典雅凝重,这在中国七大古都中是独一无二的。闲步街头,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天波杨府、包公南衙、大相国寺,……可以说,每一条街巷都深藏着一段生动的史实,每一处古建遗址都埋伏下许多迷人的故事。
我以为,一个朝代给予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抑或是淡漠的,未必和这个朝代的历时久暂成正比例,往往同当时事件的密集度、人物的知名度以及后世民众的关切度紧相联系。比如,三国时期不过几十年,可是人们却觉得绵绵无尽,为时久远,就因为斗争风起云涌,矛盾层见错出,豪杰、奸雄、智者、高人应有尽有,好戏连台,沸沸扬扬,异常热闹。宋代属于又一种情况。由于《杨家将》、《包公案》、《说岳全传》等大众文学流传广远,深入人心,在人们印象中,宋代尽多忠臣良将、义士英杰,一派河清海晏、四境承平的景象。其实并非如此。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巅峰,但已开始走下坡路。就帝王的才略来说,除了宋太祖之外,也并没有哪个是真正大有作为的。走笔至此,我倒想起一则轶事:宋初,华山道士陈抟乘白骡入汴州,途中听说赵匡胤登基做了皇帝,高兴至极,竟忘乎所以,以致从骡背上滚了下来。他说:“天下于是定矣!”还有一位自号“安乐先生”的道学家邵尧夫,写过一首《插花吟》,有句云:“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都属过甚其词。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远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乐观。北宋刚取得政权时,其统治区域只限于黄、淮流域,主要是中原一带。当时,北有契丹、北汉,虎视眈眈;西有西夏,日夕图谋东进;西南有后蜀,坐险自大;南有吴越、南汉、南唐,占据着重要经济地区,割据称雄。太祖、太宗两朝,整整用了二十年时间,才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尔后,太宗七年间两度征辽,都惨遭失败,不得不完全采取守势。到了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时,辽军大举南下,直抵汴州以北的澶州,宋廷惊恐万状,甚至拟议迁都,最后与辽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后期又面临着金人的大举入侵。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这不必说了;终北宋之世,尽管没有发生过大的内乱,但外患频仍,兵连祸结,却是公认的事实。
五
宋朝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兼为古代中国修文之高峰与武备之谷底。这和立国以来一直奉行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统治政策有直接关系。说到“轻武”,有人也许不以为然。因为在太祖、太宗眼中,“武”已经重到不能再重的程度,以致言“兵”色变,带有一种恐惧心理。这是事实。但这种重武、惧武的心态发展到极端,必然走向抑武、贬武一途。这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于是,文人就成了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文人知州,文人入相,文人管辖军队,文人能够较为随便地议论时政,在宋代,文人得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优越地位。
当然,这种“重文”,恰也说明,在宋初皇帝心目中,文人是无足轻重的,是最容易驾驭和控制的。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赵匡胤曾经说过:我用百余名儒臣分治百藩,纵使他们都去贪污,其为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将。这最露骨地道出了重文的实质。当然,历史上常常出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不管原初的用意何在,随着一系列政策、制度的确立与实施,重文轻武逐渐成为有宋一代全社会的普遍意识,客观上也推动了整个文化的发展。
所谓“守内虚外”,可从宋太宗的论述中了解个大概。他曾对近臣说过:“国家者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特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史·宋绶传》)这里反映出他对“外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终北宋之世,一直把主要兵力,尤其是为数一半以上的禁军的主力部队,放在京师与内地要冲,以防备和对付“内患”。至于北部数千里的边界线上,则只有少量兵力,又分散在多个孤立的据点上;而且,战斗力极差。
苏轼等有识之士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地指出,部队中多是一些资望甚浅的人担任将帅;而在第一线领兵的,“非绮纨少年,即罢职老校”,“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至于兵员,素质就更没法说了,“河朔沿边之师,骑兵有不能披甲上马者,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步兵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
马可·勃罗在其游记中追述前朝情景时,也曾说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决非勇武的斗士”。“皇帝本人满脑子里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自序中也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武备如此,自然无力抵御辽、金、西夏的不断侵扰。一部北宋对外作战史,充满了令人心丧气沮的溃逃、败降的记录。单是北宋与契丹的战事中,先后进行过八十一次战斗,获胜的仅有一次。每一次败绩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公元1005年,与契丹贵族订立的“澶渊之盟”,开了有宋一代以金银布帛换取屈辱和平的先河。此后,每年向辽、金、西夏输纳岁币,都在百万左右。
宋朝中、晚期,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六
开封处于南北要冲,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却又地势坦平,无险可守,作为都城,从军事角度看,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明显缺陷。但是,物产丰饶,四通八达,就经济、文化的发展来说,又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典型代表,是一座十分适合平民百姓居住,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都城。
这里,虽然不具备汉、唐国都那样宏阔的气派和规整的布局,但它也没有那种封闭式的里坊之隔,墙垣之限,因而便于沿街设市,商贸流通。而且,店铺不避官衙,所有的通衢小巷都可做为市场,就连最庄严肃穆的御街,也变得熙熙攘攘,热闹喧杂,完全从冷漠、隔绝状态中走了出来。
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奢靡、享乐之风盛行,官僚经商趋于普遍化。
立国伊始,朝廷就实行了以经济收买换取君臣相安的策略,给予一些功臣宿将兼并土地的特权,使他们可以收取巨额地租,作为官商本钱;而一般官僚仕宦也都有丰厚的俸禄,加上高利盘剥,贪污索贿,同样具备经商的条件。他们竞相动用官府车船偷税逃税,经营包括域外与禁榷的各种物资,获取高额利润。真宗朝,两浙转运使和镇州知州,在倒卖金银布帛的同时,还从事贩卖人口生意。这种雄厚资本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不仅使国家财政遭受极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严重腐败。
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初,太祖、太宗十分厌恶奢靡,恭行节俭。公元964年,北宋扫平了后蜀,亡国之君孟昶来到开封 ,献上一个装饰着七彩珠宝的尿壶,太祖见了,怒形于色,当即掷之于地,令侍从把它敲个粉碎,并气愤地对孟昶说:“一个便器就这么讲究,那么,你该用什么器具来贮藏食物?如此骄奢淫逸,怎么能不亡国!”
但是,由于建国后皇家鼓励开国功臣及时退休,蓄养歌僮舞女聊以自娱,尔后,这种风气逐渐在社会上弥漫,每逢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承欢的就是主人的家伎。仁宗朝,晏殊以宰辅之尊,日日以饮酒赋诗为乐,每会宾客,必有宴饮。从北宋的许多文人常为歌女演唱而写作,且多沿袭五代《花间集》的传统,可知一代文风是和当时的世风时尚紧相关联的。
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危急存亡之秋,朝野上下,生活方式仍然极度奢侈淫靡。汴梁城内到处布满酒楼、食店、妓院、戏场。宋代诗人刘子翚,青少年时代曾久住开封,“靖康之祸”发生后,他回故乡福建做官与讲学,忆起当年在东京的酣歌醉舞的往事,写了《汴京纪事》诗二十首,其一曰: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当时的樊楼三层高耸,五楼相向,彼此飞桥横架,明暗相通,为东京城内酒楼之最。当时,像这样的星级大酒店有七十二座,每家饮客常在千人以上。工商店铺多达六千四百家。这从《东京梦华录》和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也看得很清楚。最令人记怀的是州桥夜市,它是东京著名的景观之一。刘昌诗在《上元词》中作了生动的记述:
忆得当年全盛时,人情物态自熙熙。
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
花市里,使人迷,州东无暇看州西。
都人只到收灯夜,已向樽前约上池。
备述故都太平景象,其中已隐伏着后日的危败之由。
宋徽宗赵佶更是把这种骄奢淫侈之风推向极致,其生活之腐朽糜烂,在历代的皇帝当中,是少有其比的。他用了十多年时间,在京城东北部修起一座“万岁山”,范围超过北宋皇城的三倍。里面峰峦起伏,曲池环绕,山林蓊郁,楼阁参差,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大皇家园林。为了让这座“万岁山”有一种云雾缭绕的氛围,亲信们叫人做了许多油绢口袋,弄湿后挂在山岩上,充分吸收水蒸汽,然后把口扎上。待皇帝到来再打开口袋,水汽外溢,宛如云雾蒸腾,名为“贡云”。
为了满足以赵佶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享乐要求,特意在苏州、杭州设立了应奉局、造作局,只要发现士庶之家有奇石异木,便即用封条作记,收为皇家禁物。在淮河、汴河之中,专门运送“花石纲”的船只,舳舻相接,数月不绝。这座园林后来毁于金人的战火。人们在一座建筑的盘龙柱上刮下金屑达四百多两,其豪华富丽于此可见一斑。
元代诗人李溥光咏叹道:
一沼曾教役万民,一峰会使九州贫。
江山假说方成就,真个江山已属人。
诗句是说,万岁山建成之日,即江山易手之时。这一假一真,讽刺深刻而感慨深沉。
当时,还有一首咏《万岁山图》的七绝;
万岁纲船出太湖,九朝膏血一时枯。
阿谁种下中原祸,犹自昂藏入画图!
诗人的一腔怒气未敢直接发向皇帝,结果对着假山放了一通火炮,但其抨击的效果却是一样的。
七
综观有宋一代的兴衰史,益发相信鲁迅先生的警辟的睿断。他说,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的”;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完。在隋代,“讨债的”炀帝杨广紧跟在“还债的”文帝杨坚脚后出现,结果二世而亡。赵匡胤创业一百四十年后,才出现赵佶这班“讨债者”,此亦北宋不幸中之幸也。
汴梁城毁于金人战火,加上后来几次黄河泛滥,致使往日的千般绮丽,万种繁华,一股脑地被深埋地下。前面说过的那座“州桥”,当时汴河流经其下,天街贯穿南北,备极繁华之盛,不然,“青面兽”杨志也不会跑到那里去卖刀。可是,这次在开封,当我要寻觅它的踪迹时,东道主却说,遗憾得很,它已经隐匿在五米土层之下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毕竟是“往事越千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城面貌,说是宋城旧迹,其实,乃是清代的孑遗。
英国文学名著《简爱》的女主人公重回故地桑菲尔德府,目睹物是人非之惨景,曾喟然叹道:一切没有生命的依然存在,而一切有生命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尽管这话十分警辟,但却并不准确,没有生命的同样也在变化。一千多年前,李白写过一首《梁园吟》,有句云:
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
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
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
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
说的是山河犹是,人事已非。于今,不要说梁园、万岁山,连那滔滔滚滚的汴水也已荡然无存,早就淤成了平地,只剩下“汴水秋声”四个字,作为“汴京八景”之一,留存在方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