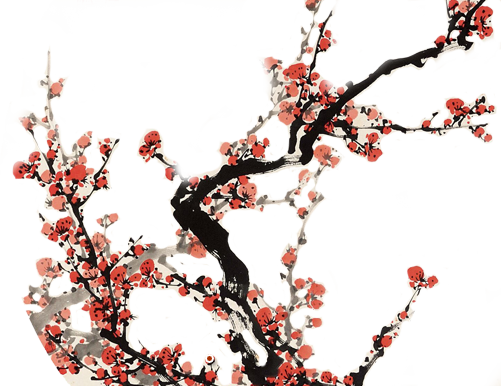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叩 问 沧 桑
一
洛阳为“天下之中”,这句话出自古代的大政治家周公之口。我们华夏之邦号称“中国”,据说就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
今天,站在这块厚实、沉重的土地上,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傲睨自大,谈不到;无动于衷,也不是。大概于眉间睫下,总流露着几分惊叹,几许苍凉吧?
从距今近四千年的夏王朝开始,到五代时的后梁、后唐、后晋为止,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在中国七大古都中,洛阳是最先形成城市并贵为国都的,而且建都历时最久,至少在一千一百年以上。华夏的先民在以邙山和洛河为依托的东西近四十公里的范围内,为中国以至整个世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其历史遗迹、人文景观之盛,实为世所罕见。
历史上有“五都贯洛”之说,“五都”指的是夏都、商都、周代王城、汉魏洛阳故城和隋唐东都城,它们东西相连,错落有致,在形制、布局及宫殿的配置上,体现出较强的连续性。从这里不仅能够看到洛阳城市发展的一条鲜明的脉络,而且,透过历代都城的沧桑变化,也可以从中略览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缩影。所以,北宋大政治家、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有诗云:“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当然,由于岁月湮沉,兵燹摧毁,这里已经不见了巍峨的宫阙、高耸的城墙,不见了金碧交辉的画楼绣阁、古刹梵宫,不见了旧日的千般绮丽、万种繁华。就地面上的遗存而言,实在无法与欧洲的“永恒之城”罗马相比。那座“永恒之城”称得上是一座露天的古代建筑博物馆,孤零零的白色大理石圆柱,长满青苔的喷泉底座,四壁萧然的庙宇残墙,倒塌了一角的庞然高耸的圆形竞技场,还有几座基本完好的凯旋门,这些千余年前的旧物,在无言而雄辩地向过往行人宣示着人类在建筑艺术方面已经达到的高超水准,展现着古罗马往日的壮丽与辉煌。
东西方这两座名都的古代建筑,在地面遗存上竟有如此鲜明的反差,探究起来也是很有趣的。我想,可能取决于下列几个因素:
从环境思想、建筑观念上看,中国自始即接受“新陈代谢”的哲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对于原物的存废、久暂考虑得并不多,不像古代埃及、罗马那样刻意追求所谓永久不灭的工程。观念影响实践,当古罗马以至世界多数地区逐渐地以石料取代原始木构,建筑进入“岩石文化”之时,而中国却始终保持着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的习惯,古都洛阳的建筑自然也不例外。
从地理位置、地形条件上看,洛阳四周凭险可守,有“居中御外”之便,自古战乱连绵,为兵家必争之地,而罗马的地理形势与此不同;又兼罗马素有“七丘城”之称,古建筑大都在高丘之上,不像洛阳那样“背邙面洛”,地势坦平,以致熏天烈炬,四野灰飞;掠地浊流,千村泥塞,许许多多的文物都毁于兵燹、水火。
当然,这并不影响人们到这里来临风怀古,叩问沧桑。历史的生命力总是潜在的或暗伏的。作为一种废墟文化,只要它有足够的历史积淀,无论其遗迹留存多少,同样可以显现其独特的迷人魅力,唤起人们深沉的兴废之感,吸引人们循着荒台野径、败瓦颓垣,去凭吊昔日的辉煌。
废墟是岁月的年轮留下的轨迹,是历史的读本,是成功后的泯灭,是掩埋着千般悲剧、百代沧桑的文化积存。由于古代中国的史籍提供了足够的甚至是过量的信息,即使面对残墟野圹的“旧时月色”,熟悉古代文化传统的作家、诗人,也能以一缕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旧日的华采。
对于专门从事废墟研究的学者,罗马古都当然是必看无疑了,但我以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古国可能会给他们提供更丰富的内涵;而若到中国来,首先应该在洛阳住上一些时日,感受几许壮美后面的沉痛与苍凉。对于诗人来说,尤其是如此。诗人往往比史家更关注现实与古昔撞击之后所产生的人生体悟,更加强调创作主体自我情绪的介入,也更看重历史选择、历史创造后面所闪现的人民生命活动的一次又一次的升华。
二
现在,我正站在汉魏故城遗址之上。城址在今洛阳市东北十五公里处,北依邙山,南临洛河,东至寺里碑,西抵白马寺,地势高亢平旷,规模宏阔壮观。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朝先后以此为皇城,长达三百三十年之久。
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在周代成周城的基础上,开发扩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广建宫殿、苑囿,台、观、馆、阁。在这里,“天子之庙”明堂,“天子之学”辟雍,观测天象、祭祀天地的灵台,以及相当于今天国立大学的太学,一应俱全。
当时,城内有纵横二十四条大街,长衢夹巷,四通八达。帝族王侯,外戚公主,争修园宅,竞夸豪丽。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阁生风,重楼起雾,极尽奢华之能事。可是,经过汉末董卓人为性的破坏,顷刻间宫殿便全部化为灰烬,“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西晋的“八王之乱”,进一步造成了“河洛丘墟,函夏萧条”。
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后,再次大兴土木,城东西扩至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规模空前。仅寺院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皇宫西侧永宁寺,九层佛塔加上顶端相轮,高达百丈;僧房多达一千间。永明寺内住有“百国沙门”三千余人,城中外国商旅万有余家。整个洛阳城已成为盛况空前的国际性大都会。后经尔朱荣之乱,造成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隋、唐两代对东都城都曾相继加以恢复,但“安史之乱”又使洛阳再一次惨遭洗劫,宫室焚烧,十不存一。
今日登高俯瞰,但见残垣逶迤,旧迹密布,除南面已被洛河冲毁外,其余三面轮廓均依稀可辨。残垣共有十四处缺口,标示着当时“楼皆两重,朱阙双立”的城门所在。城址四周矗立着一排排直干耸天的白杨林,里面围起来一方广袤的田野,翻腾着滚滚滔滔的麦浪。“白杨多悲风”,更加重了废墟的苍凉意蕴,使游人看了频兴世事沧桑之感。
说到世事沧桑,我蓦然联想起意大利的另外一座古城的命运。就在我国东汉王朝的洛阳城兴建起来之后,靠近那不勒斯海湾,离维苏威火山不足两公里的庞贝古城,突然被亿万吨的火山灰埋没了,其时为公元79年一个初秋的正午。
从此,这座古城便从地面上消失,终古苍凉,杳无声息,多少代的人们把它遗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一千多年之后,历史学家才从古书中发现这样一座已经不复存在的城市,但却说不清楚它的具体位置。公元1748年,当地农民在挖掘葡萄园时,偶然发现一些碑碣、石像,这才提供了一些线索。又经过二百多年的陆续发掘,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才使庞贝古城重见天日。相形之下,中国一些古都的命运要好一些。
当年,殷商的遗民箕子朝周,路过安阳殷墟,见旧日的宫殿倾圮无遗,遍生禾黍,哀伤不已,因作《麦秀》之歌。西周灭亡之后,周大夫行役至于镐京的宗周旧邑,满眼所见也都是茂密的庄稼,不禁触景伤怀,遂吟《黍离》之诗。这两首歌诗便成为后世有名的抚今追昔、凭吊兴亡、抒发爱国情怀的佳什。
同《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相对应,在洛都还流传着一个关于“铜驼荆棘”的预言的警语。晋惠帝时,以草书闻名于世的索靖,具有逸群之才和先识远见,他觉察到天下就要大乱,于是,指着宫门外两个相向而立的铜铸的骆驼,喟然叹道:人们将会看到你们卧在荆棘中啊!不久,洛阳宫苑即毁于“八王之乱”。 “不信铜驼荆棘里,百年前是五侯家”。元人宋无这两句诗,说的正是这种变化。
看来,世事沧桑毕竟是人间正道。所以,东坡先生慨叹:物之盛衰成毁,相寻于无穷,昔者荒草野田,狐兔窜伏之所,一变而为台囿,而数世之后,台囿又可能变成禾黍、荆棘,废瓦颓垣。“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
至于洛阳园囿之兴废,尤其寓有特殊的意蕴。宋代学者、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有一句名言:“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就洛阳当时在中国的形势、地位来看,这种论说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三
魏晋时期有一种特别显眼而且层见迭出的政治现象,就是异姓禅代,美其名曰“上袭尧舜”,实际是曲线谋国。
公元219年(汉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被曹操打败,上表称臣,并奉劝曹操称帝。篡汉自立,位登九五,这是曹操梦寐以求的事。孙权的劝进,在他来说,自是求之不得的。事实上,汉朝早已名存实亡,曹操手握一切权力,献帝不过是任其随意摆布的玩偶。只是慑于舆论的压力,曹操始终未敢贸然行事,不得不把皇袍当作内衣穿了二十多年。
当下,他就找来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试探一番,说:孙权这小子劝我称帝,这简直是想让我蹲在火炉上受烤啊!司马懿心里是透彻明白的,立即迎合说,这是天命所归,天随人愿。但是,没有等到称帝,曹操就一命呜呼了,大业要靠他的儿子完成。曹丕继位之后,经过一番“假戏真做”的三推四让,便于公元220年登上了受禅台。
此后,司马氏祖孙三代,处心积虑,惨淡经营,心里想的、眼睛看的、天天盼的,仍然还是皇位。终于在公元266年,司马炎完全按照“汉魏故事”进行禅代,从魏元帝曹奂手中夺得了皇权,是为晋武帝。一百五十五年以后,宋主刘裕依样画葫芦,接受了东晋恭帝的“禅让”,即皇帝位。一切处置“皆仿晋初故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第二年就被刘裕杀掉了。
从公元220年曹魏代汉到公元420年刘宋代晋,二百年“风水轮流转”,历史老人在原地划了一个魔圈。三次朝代递嬗,名曰“禅让”,实际上,每一次都是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而且伴随着残酷、激烈的流血斗争。
晋承魏统,实现了九十年分裂混战之后的重新统一。但是,由于西晋统治集团的骄奢淫佚,腐朽残暴,导致这个王朝仅仅维持了五十二年。特别是标志着统治集团矛盾全面爆发,骨肉相残成为历史之最的“八王之乱”,持续时间之长,杀人之多,手段之残忍,对生产力破坏之严重,在中外都是罕见的。
司马炎在位二十五年,死后由“白痴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惠帝。他只是“聋子的耳朵——配搭”,实权掌握在骄横跋扈的外祖父杨骏手中。而野心勃勃、阴险凶悍的皇后贾南风和其他几个皇室成员,也要争夺最高权力。从此,西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就拉开了大幕。
贾皇后联络了几个忌恨杨骏的藩王和大臣,通过制造杨骏谋反篡位的舆论,逼令惠帝颁下讨伐诏书,一举捕杀了杨骏及其亲属、死党,诛灭三族达几千人。尔后,召令汝南王司马亮入京,与开国元老卫瓘共同辅政,借以掩饰后党掌权的真相。不料,司马亮专横跋扈,不给贾皇后一班人留下权力空隙,于是,皇后再次逼迫惠帝颁诏,命令楚王司马玮杀掉司马亮,同时,趁机除掉了重臣卫瓘。为了防止重新出现藩王专权的局面,贾皇后又以“专杀”的罪名处死了剽悍嗜杀的司马玮。就这样,卸磨杀驴,获兔烹狗,贾皇后一个个地铲除了元老、强藩,达到了独揽朝纲的目的。
当时面临的最大课题,是由谁来继位接班。贾皇后骄横妒悍,却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才气与胆识,她不敢设想自身临朝问政,但又绝不甘心由已定的东宫太子继承皇位。经过一番周密策划,终于把太子椎杀了。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只好声称是太子自裁,于是,扮演了一场“猫哭老鼠”的闹剧,哀恸逾常,并以王礼下葬。
但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贾后谋杀太子的阴谋败露后,赵王司马伦联合宗室的齐王、梁王,大动干戈,入京问罪,当即捉住贾后,逼着她喝下一杯金屑酒。临死前,贾后恨恨地叹着气,说:拴狗要拴狗脖子,我却只拴了狗尾巴;杀狗要杀老恶狗,我却只杀了几只狗崽子。老娘今天死了,算是活该!
司马伦野心勃勃,凶残毒狠,一面大开杀戒,乘机把所有的冤家对头一一送上刑场,一面将他的几个儿子全部封为王侯,自己出任相国,接着,就从惠帝手中夺取了御玺,称帝自立。尔后,又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官雨”,不仅遍封了徒党,而且,连拥戴他的奴隶、士卒也都赏赐爵号,一时受封者达数千人。这又引发了齐王、成都王、河间王联合起兵讨伐,战火燃遍了黄河南北。司马伦兵败被杀,惠帝重登皇位。
这次祸乱,持续了六十多天,死亡达十万人之众;而诸王之间又相互混战,结果有的被砍头,有的被放在烈火上烤焦,有的被绳子勒得断了气,有的被活活掐死,诸王竟无一善终。
“八王之乱”始于宫廷内部,由王室与后党之争扩大为诸王之间的厮杀;尔后,又由诸王间的厮杀扩展成各部族间的混战。这场狂杀乱斗,足足延续了二十多年,西晋政权像走马灯一般更迭了七次。先后夺得权柄的汝南王、赵王、齐王、成都王、东海王,以及先为贾后所利用、随后又被贾后杀掉的楚王等,无一不是凶残暴戾的野心家、刽子手。在他们制造的祸乱中,“苍生殄灭,百不遗一”,京都洛阳和中原大地的劳动人民被推进了茫茫的苦海深渊,最后导致了十六国各族间的混战和持续三百年的大分裂,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一次大的曲折和倒退,其罪孽是异常深重的。
四
司马氏以禅代手段建立的西晋王朝,是极度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有的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荒淫、颓废等龌龊行为,都集中地表现在这个统治集团身上。晋武帝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登极后,即选征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里的大批处女入宫;次年,又从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中选征了五千名处女;灭吴后,又从吴宫宫女中选取了五千人。皇帝淫乱在上,士族和官吏自然也是竞相效尤,淫靡成风。
由于朝廷的狂杀与滥赏,使得周围的官员感到得失急骤,祸福无常,心情经常处于紧张、虚无状态,助长了纵情声色,颓废、放荡。晋武帝率先倡导奢侈享受,夸靡斗富,他的亲信和大臣很多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奢侈无度的人。开国元老何曾,一天花在三顿饭上的钱要在一万以上,还说没有可以下箸的东西。他的儿子何劭日食两万钱,比老子翻上一番,可是,这还不够尚书任恺两顿饭的花费。而王济、王恺比任恺更为穷奢极侈。但他们又谁都比不过石崇。
大官僚石崇,“资产累巨万金,宅室舆马,僭拟王者。庖膳必穷水陆之珍,后房(妻妾)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而丝竹之艺,尽一世之选。筑榭开沼,殚极人巧。”他和武帝的舅父王恺斗富,王恺用紫丝布作成布障,衬上绿绫里子,长达四十里;他则用锦缎做成长达五十里的布障来比阔。武帝看王恺斗不过他,便常常出面相助。这也是旷代奇观。翻遍了史书,哪曾见过皇帝帮助臣下夸侈斗富的?即此,也足以想见当日奢风之盛行,朝政之腐败。
一次,王恺拿出皇帝给他的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借以夸富。这棵珊瑚树枝叶繁茂,他以为,世上很少能够与之相比的。不料,石崇看后,操起铁如意来就把它敲个粉碎,随后,便招呼手下的人把他收藏的珊瑚树全都搬出来,任他随意挑选。就中有六、七棵三尺、四尺高的,枝条层层重叠,美艳无双,光彩夺目。王恺看了,顿时眼花缭乱,两颊飞红,惘然自失。
退休后,石崇在洛城的金谷涧,顺着山谷的高低起伏,修筑了一座占地十顷的豪华别墅,取名梓泽,又称金谷园。飞阁凌空,歌楼连苑,清清的流水傍着茂密的丛林,单是各种果树就有上万株,风景绝佳,华丽无比。“楼台悬万状,珠翠列千行;华宴春长满,娇歌夜未央。”(张美谷:《金谷名园》诗句)人们用“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话来夸赞其高超的建园艺术。
其时,炙手可热的赵王司马伦当政,石崇由于把持爱妾绿珠不放,得罪了权臣孙秀,被诬为唆使人谋杀赵王伦,受到了拘捕,绿珠坠楼而死;石崇及其兄长和妻子、儿女等十五人一齐在东市就戮;钱财、珠宝、田宅、奴仆无数,悉被籍没。就刑前,石崇慨然叹道:想当年我老母去世时,洛阳仕宦倾城前来送葬,摩肩接踵,荣耀无比。今天却落到这个满门遭斩的下场!其实,我没有什么罪。这些奴辈要我死,无非是为了侵吞我的全部资财!他的话一落音,看押他的兵士就问道:既然你知道万贯家财是祸根,为什么不早日散尽呢?石崇哑然无语。
金谷园千古传扬,在洛阳可说是妇孺皆知,可是,要考察它的遗址所在,却是众说纷纭。这天,我在一位饱学之士陪同下,沿着邙山南麓,信步走到凤凰台村,顺着金谷涧东南行,据信,当年的金谷园就坐落在这个范围里。而今,除了细水潺潺,悠悠远去,一切一切,都已荡然无存。真个是:“豪华人去远,寂寞水东流。”早在初唐时期,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已经慨叹“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何况今天,毕竟已经过去一千七百多年了。
五
站在北邙山上,纵目四望,但见上下左右,陵冢累累,星罗棋布,怪不得人说“邙山无卧牛之地”。唐代诗人王建有诗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
原来,这里眼界开阔,地望极佳,身后有奔腾不息的黄河滋润,迎面有恢宏壮观的帝京映照,地势高爽,土层深厚。俗谚云:“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因此,自东周起,中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直至五代,历代帝王陵墓比邻而依。就连“乐不思蜀”的刘禅,被称为“全无心肝”的陈叔宝,“终朝以眼泪洗面”的李煜,这三个沦为亡国贱俘的后主,也都混到这里来凑热闹。其他名人,像伊尹、吕不韦、贾谊、班超……简直数不胜数,都把此间作为夜台长眠之地。踏着黄沙蔓草,置身于累累荒丘之间,确实有一种阴气森森,与鬼为邻的感觉。
听说西晋王朝的五个帝王,也都葬在这里,这天,我专程转到了这一带,想要看个究竟,结果竟一无所获。原来,足智多谋的司马懿担心墓葬会被人盗掘,临终前嘱咐子孙,不起坟堆,不植树木,不立墓碑。这比曹操死后遍设七十二疑冢还要来得神秘,真是至死不脱奸雄本色。
这种形制影响到整个西晋王朝,所以,司马懿父子三人,连同四代帝王,以及统统死于非命的“八王”的陵寝所在,直到今天还是一个疑团。为了一顶王冠,生前决眦裂目,拚死相争,直杀得风云惨淡,草木腥膻,死后却连一个黄土堆也没有挣到自己名下,说来也是够可怜的了。当然,那些臭皮囊早已与草木同腐,有一些人甚至“骨朽人间骂未销”,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知不知其埋骨地,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正是由于这里“地脉”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娇妻美妾都齐刷刷、密麻麻地挤了进来,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无论生前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最后统统地都在这里碰头了。像元人散曲中讲的,“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纵有千年铁门槛,终归一个土馒头。
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也讲了,他在剧作《哈姆莱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说,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谁知道亚历山大帝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莱特接着唱道:“凯撒死了,你尊贵的尸体/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
莎翁在另一部剧作里,还拉出理查王二世去谈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稽剧。我以为,他是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劝诫人们不妨把功名利禄看得淡泊一些。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耐人寻味。
而在中国古代作家的笔下,就显得特别直白、冷隽、痛切。旧籍里有一则韵语,讥讽那些贪得无厌,妄想独享人间富贵、占尽天下风流的暴君奸相:“大抵四五千年,着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
马东篱在套曲《秋思》中沉痛地点染了一幅名缰利锁下拚死挣扎的浮世绘:“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蝇争血。”“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他分明在说,历史,存在伴随着虚无;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看来,谁也不是,而是历史本身。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在无尽感慨中,我口占了四首七绝:
圮尽楼台落尽花,谁知曾此擅繁华?
临流欲问当年事,古涧无言带浅沙。
残墟信步久嗟讶,帝业何殊镜里花!
叩问沧桑天不语,斜阳几树噪昏鸦。
茫茫终古几赢家?万冢星罗野径斜,
血影啼痕留笑柄,邙山高处读南华。
民意分明未少差,八王堪鄙冷唇牙。
一时快欲千秋骂,徒供诗人说梦华!
六
魏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动荡时期。攘夺、变乱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统治集团内部篡弑频仍,政权更迭繁复,战乱连年不断,社会急剧动荡,给普通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苦痛,士人群体也未能远祸。因此,《晋书》中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当时的社会思想十分错综复杂。一方面是,汉末以来,曹操四次下求贤令,实行“唯才是举”的政策,即使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盗嫂受金”,甚至“不仁不孝”者,只要有才能,都可以推荐上来,委以重任。这种由道德至上到重才轻德的转折,无疑成了魏晋时代思想解放的先声。
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世家权贵操纵着遴选人才大权,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悖理现象。先赋角色深受世人景慕,而成就角色却极少出头机会,在整个社会造成了价值观念的误导,鄙薄事业、轻视功利的思想泛滥。这两种趋向,看似矛盾、交叉,实则殊途而同归,都有助于以崇尚老庄,任放不羁,遗落世事为特征的“魏晋风度”的形成。
由于思想通脱,废除固执,“遂能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而入”(鲁迅语)。社会秩序解体,儒家礼法崩溃,经学独尊地位已经动摇,玄名佛道,各派蜂起,嘘枯吹生,逞辞诘辩,呈现出“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思想多元化的局面。
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语)。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蔑视礼法,荡检逾闲,秕糠功名利禄,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滋生了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的萌芽。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其代表人物。
阮籍尝登荥阳广武山,观楚汉战场,慨然叹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自然是话中有话:一则借助谩骂以玩弄权术起家的刘邦,影射那些包括司马氏在内的得势于一时的风云人物;二则也是愤激于生当乱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们这些名士空负英雄之志,而无由酬其夙愿。
按常礼,母丧期间必须茹素,但阮籍偏偏大啖酒肉。《礼记》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经常与嫂子聊天,其“嫂尝归家,籍相见与别,或以礼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耶?’”邻居家的妻子有美色,在酒店里卖酒。阮籍喝醉以后,就睡在这个女人身边,完全无视儒家“男女之大防”。女人的丈夫起初有些怀疑,暗中观察阮籍的行为,但始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良企图。
他就是这样毫无顾忌地与纲常、礼教对着干.,明确地说,君子之礼法乃天下摧残本性、乱危社会、致人窒息之术。阮籍和嵇康率先举起张扬自我、反对名教的大旗。阮籍辛辣地讽剌说,礼法之士如裤中之虱,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嵇康则响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
如果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与司马氏统治集团开展斗争的一种形式。鲁迅先生指出,魏晋以孝治天下。因为他们的天位乃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则立脚点不稳,立论既难,办事也棘手。于是,他们倡言以孝治天下,把名教作为剪除异已,巩固政权的工具,充分暴露了这种名教与礼法的虚伪性。阮籍、嵇康等公开抨击名教,蔑视礼法,无异于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司马氏,当然要引起当权者的忌恨。
特别是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列举了“七不堪”、“二不可”,来说明作了官就会妨碍个性发展与个人自由,实际是表明不肯为司马氏卖命的心迹。他在《卜疑》一文中更加露骨地讲:人们都说商汤王、周武王用兵的功劳有多大,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如何好,尧舜禅让之德多么美,孔老夫子的话怎样有理,依我来看,这一切都是虚伪的。
此时的司马昭正在标榜自己武功盖世,辅助魏帝多么忠心耿耿,暗地里却处心积虑地筹划着如何搭设“受禅台”。嵇康上面那番话,针锋相对,恰中要害,不啻一记响亮的耳光,自然要遭到司马氏集团的痛恨。终于被安上一个罪名,一杀了之。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鲜血淋漓的教训,造成那些名士、畸人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有意无意地出现一些畸形的变化。他们的人生以悲剧垫底,但却表现出常人所难以理解的旷达和潇洒,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加之,伴随着旧的权威思想的崩溃,人们在信仰、追求、价值取向方面失去了依归,经常陷于精神空虚与紧张、焦虑、孤独之中,导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和联系纽带的断裂。阮籍有一首《咏怀诗》,对他内心的苦闷和临深履薄的心态作了最生动的揭示: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竹林名士经常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这是他们思想、性格上的外在表现的重要形式;而全身避祸,醉以忘忧,“欲将沉醉换悲凉”,则是其深层的考虑。对此,宋人叶梦得看得最清楚,他在《石林诗话》中指出:“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司马昭为了把阮籍拉进自己身边,要娶他的女儿作儿媳。阮籍却不愿攀上这门亲戚,但又不敢公开拒绝,就从早到晚喝酒,醉倒就睡,睡醒又喝,连续醉了六十天,媒人无可奈何,不得不怅然走开,司马昭也只好作罢。
刘伶更是出名的酒鬼,经常豪饮,任性放纵,有时在屋里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别人看见了加以讥讽。他却说,我把天空和大地作为屋宇,把房舍作为裤子,诸位先生怎么跑到我的裤裆里来了?他在散文名篇《酒德颂》中说:“兀然而醉,恍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惟酒是务,焉知其余”。
山涛“至八斗方醉”;阮咸饮酒“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他们借助酒力来表达对当权者的蔑视与反抗,摆脱世俗礼制的束缚。其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乐趣,不过是一种无奈与无聊罢了。
七
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呈现出多元、混乱、无序、开放状态。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是儒学的禁锢渐近衰弛,个体的智慧才情得到了充分的承认与重视。文人、学者们开始集中地对人的个性价值展开了探讨与研究,个性解放的浪潮以锐不可挡之势,冲破了儒学与礼教的束缚。一时,思想空前活跃,个性大为张扬,防止了集体的盲目,增强了创造、想象的自主性,开始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又兼各民族之间战事连绵,交流广泛,作家、诗人生计艰难,流离转徙,丰富了阅历,深化了思想,从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
时代的飙风吹乱了亘古的一池死水。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文学的大幸、美学的大幸,成就了一大批自由的生命,成就了诗性人生。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迸射出生命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值得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生命自由的时代,留下了文化的浓墨重彩。清代诗人赵翼在《题元遗山集》中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之句,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道理。当然,这也正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伟大诗人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魏晋文化跨越两汉,直逼老庄,接通了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血脉,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行动起来,自觉地把对于自由的追寻当作心灵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飞扬。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魏晋时代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更感到审美人生的建立,自由心灵的驰骋,是一个多么难以企及的诱惑啊!
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范文澜语)由于曹氏父子倡导于上,加之本人都是大文学家,当时又具备比较丰裕的物质生活和有利的创作环境,那些饱经忧患、心多哀思的文士们,创作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于是,建安才士源源涌现,多至数以百计,他们的诗赋骈文,特别是以曹植为代表的五言诗,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邺下风流在晋多”。西晋一朝,动乱不宁,为时短促,但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却是巨大的。钟嵘说,太康(晋武帝年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亦文章之中兴也。一时文华荟萃,人才辈出,流派纷纭,风格各异。继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之后,活跃在文坛上的正始诗人、太康诗人、永嘉诗人,薪尽火传,群星灿烂。
尤其是以赋的成就为最大。左思《三都赋》一纸风行,时人竞相传抄,遂使洛阳纸贵。陆机的《文赋》,不仅是一代文学名作,而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献。竹林七贤多有名篇佳作传世,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他们的《咏怀》诗、《大人先生传》和《幽愤诗》、《与山巨源绝交书》,一直传诵至今。“金谷二十四友”中为首的潘岳,与陆机齐名,是“太康体”的代表性作家,为西晋最有名的诗人,三首《悼亡》诗,笔墨之间深情流注,真切感人。
魏晋时的史学、哲学、书法艺术成就可观。陈寿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被历代史家誉为最好的正史之一。西晋玄学、佛、老,对后世有颇深的影响。嵇康、邯郸淳等书写的古、篆、隶《三体石经》,乃世所罕见的书艺珍品,钟繇的楷书也是独擅盛名。
就在那些王公贵胄、豪强恶棍骸骨成尘的同时,竟有为数可观的诗文杰作流传广远,辉耀千古。这种存在与虚无的尖锐对比,反映了一种时代的规律。
事物总是错综复杂的,上下相形,得失相通,成败相因,利弊相关。人的一切社会成就的获得,往往会造成他作为个人的某些方面的失去;而表面上看来是失败的东西,其反面却又意味着成功。从社会时代来考究,嵇康、阮籍等人都是失败者,都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但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看,却又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八
魏晋故城遗址东面,建春门外一里多路的东石桥南有个马市,旧称东市,是魏晋时期行刑的场所。这次,我特意到那里转了转,已经是荒草没胫,面目全非了。当年,嵇康临刑前,曾把他的琴要过来,坐在地上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亲友们听了那激昂、凄厉的琴声,个个泣下不止。嵇康只是长叹了一口气,说:这支曲子是一位老先生教给我的,当时我们在旅途中,同住一间客栈。他再三嘱咐我,不要另传他人。可惜,从今以后,它就将失传了。有人考证,这个《广陵散》原是一首古曲,内容是表现战国时期聂政剌杀韩相侠累、兼中韩王的。临死时,嵇康还要奏这种曲子,说明他胸中的愤懑不平之气,该是何等强烈。
嵇康殁后,在缅怀他的诗文中,最撼人心弦的当推向子期的《思旧赋》。嵇康被杀,他的好友向子期再也无法隐居了,只好出来入仕,投到司马氏门下。这天,他归自洛阳,路过嵇康的山阳故居(在今河南修武县),触景伤怀,写下了正文只有二十四句的小赋。在那闪烁其词、欲说还休的寥寥数语中,人们感受到一种欲哭无泪、深沉得近于心死的悲哀。其中有这样的话:“叹《黍离》之悯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蹰。”竟将区区山阳故居的荒凉,与周室、殷墟之破败相提并论,显现出向子期的深沉的故国之思和对从前隐逸生活的眷念。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