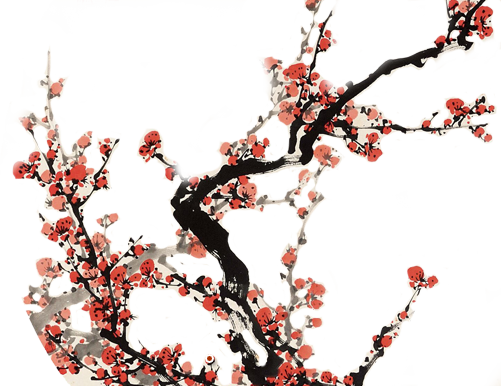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王充闾
世间的书有两种,一种是“有字书”,一种是“无字书”。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他自己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不仅视书本为生命,直到临终前还坚持阅读;同时也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通过“走万里路”向社会学习,向人民学习,吸收各方面活的知识,即所谓读“无字书”。“有字书”,尽管卷帙浩繁,远不止“汗牛充栋”,但毕竟还能以卷数计算;而“无字书”则充塞宇宙、囊括古今、遍布社会、总揽人生,是任何手段、任何仪器也无法计量的。
读“无字书”,自然包括旅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旅行为重要以至基本途径。特别是那些名城胜迹、名山大川,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文人骚客留下较多屐痕、墨痕的所在。千百年来,那些文人墨客,凭着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感受力,写下了难以计数的诗文墨迹,为祖国的山川胜景塑造出画一般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象和脍炙人口的华章隽句;使得后人足迹所至,随处都有相应的诗文和轶闻、佳话,见诸方志,传于史简,充盈耳目,任你展开垂天的思维羽翼去联想与发挥。实际上,在你亲游身历之前,通过读“有字书”所形成的无数诗文、轶事的积蓄,已经使你不期然地背负上一笔情思的宿债,急切地渴望着对其中实境的探访,情怀的热切有时竟会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
这样一来,当你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观赏现实的景物,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有厚度的艺术世界。像读“有字书”一样,通过认知的透镜去观察历史,历练人生,体验世情,从而获得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彩的效果。种种民族兴废、世事沧桑、家国情怀的鸿爪留痕,在时空流转中所显示的超出个体生命的意义,都在新的环境中豁然展开,给了我们无尽的追怀与感慨。
这是历史,也是诗章,更是哲学,是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人们既从历史老人手中接受一种永恒悲剧的感怀,今古同抱千秋之憾,与山川景物同其罔极;又同时从自然空间那里获取一种无限的背景和适意发展的可能性,感悟到人不仅由自然造成,也由自己造成;不仅要服从自然规律,也能利用自然规律;人死复归于自然,又时刻努力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
一说历史、哲学,人们往往都会想到那些“十三经”、“廿四史”,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什么古老的语言、悠远的年限和深奥的密码,总之,离开现实生活很远,既深邃又神秘,只有走进图书馆、博物馆,一头钻进故纸堆里,才能有机会和它打个照面。实践表明,真正有价值、有准备的旅行——而不是那种群行群止的集体出游,逐个景点匆匆“点卯”,然后“咔嚓咔嚓”,留下几张照片,就算了事——同样可以收到阅读的奇效。
最近,读过一篇汪涌豪教授关于论述旅行哲学的文章,深获教益。汪文指出,一切多情又深于情的人都把旅行当作修行,当作岁月的清课,精神的受洗。他们不仅从学理上驳正20世纪以来仅从经济角度界定旅行的粗浅认知,还原其作为各种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的复合体的实相,更持一种文化论立场,凸显其背后所蕴藏的诗的本质与哲学的品格。如英国人约翰·特莱伯就视哲学为旅行的关键性基础。其实,还有好多更深刻的知见,长久以来都被人忽视了,我说的是类似诺瓦利斯这样的天才诗人,他曾说:“哲学原就是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或许,还有中国诗人白居易的“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他们其实都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旅行的认知,告诉人旅行走的是世路更是心路,而那个可称“归处”的“家园”与人的实际占籍无关,它只是让人回到自己的诗意栖居。因此,与其说它是集远离与回归于一体,毋宁说更是回归。正如与其说它是消耗,毋宁说是滋养;是付出,毋宁说是获得。它是颠簸中的安适,转徙中的宁静,是在过去中发现当下,在自然中发现人性,在一切看似与己无关的人事中发现自己。当你真正有了这份切实的体悟,你就迎来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节点——你终于懂得,什么叫人走向内心世界的路,要远比走向外部世界悠长得多。
二
就一定意义上说,赏鉴自然风景、游观大千世界,实际上,无异于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开拓心境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当然,更如汪教授所言,同时,人们也是在从中寻找、发现和寄托着自己。
在这里,我们与传统相遭遇,又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它,于是,历史就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为我们解读当下、思考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此刻,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会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而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这种情志包括了对古人的景仰、评骘、惋惜与悲歌,闪动着先哲的魂魄,贯穿着历史的神经和华夏文明的汩汩血脉。
历史老人和时间少女一样,都是人类自觉地存在的基本方式,是随处可见,无所不在的。比如,我在江苏吴江的同里、周庄这两个江南名镇里,就曾同历史老人不期而遇,觉得它们都有说不尽的话题。像对待“有字书”一样,我的当务之急,或者说我所集中思考的问题,同样是如何认知,如何解读,怎样分析这些历史话题。
在前往同里的汽车上,听司机讲了它的“命名三部曲”:由于交通便利,灌溉发达,土壮民肥,同里最初的名字叫作“富土”;后来人们觉察到这样堂而皇之地矜夸、炫耀,不太聪明,既加重了税负,又无端招致邻乡的嫉妒,还经常不断受到盗匪、官兵的骚扰,于是,就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把“富土”两个字叠起了罗汉,然后动了“头上摘缨,两臂延伸”的手术,这样,“富土”就成了“同里”;十年动乱期间,为了赶“革命”的时髦,造反派曾经赐给它一个动听的名字,叫“风雷镇”,但是,群众并不买账,为时很短,人们就又把它改回来了。你看,简简单单的一个镇名,就经历了这般奇妙的变化,焕发出许多文采,真应赞叹这“无字书”的意蕴丰盈。
在周庄,看了几处历代名人宅第。船出双桥,拐进了银子浜,就见到一个沿河临街的大宅院。舍舟登岸,跨进前厅,看到门额上标着“张厅”二字。原是明代中山王徐达之弟徐孟清的后裔于正统年间兴建,清初为张姓所有。南行不远,就到了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后人建于乾隆初年的敬业堂,现在习称“沈厅”。走进了这处七进五门楼,一百多间房屋,占地两千多平方米的豪宅,人们自然免不了感慨系之地谈论一番沈家的兴衰史。
沈万三的祖上以躬耕垦殖为业,到了他这一辈,借助此间水网条件进行海外贸易,从而获利无数,资财钜万,田产遍于四方,富可敌国。无奈,做生意他虽称高手,可是,玩政治却是一个十足的笨伯。他同所有的暴发户一样,见识浅短,器小易盈,不懂得封建政治起码的“游戏规则”,一味四处招摇,不肯安分守常,结果,接二连三干下了种种蠢事,最后竟招致杀身惨祸。性格便是命运,信然。为了拍皇上的马屁,沈万三晋京去奉献什么“龙角”,还有黄金、白金,甲士、甲马,并斥资建筑了南京廊庑、酒楼。这下可爆出了名声,显露了富相。恰似“欲渡河而船来”,朱元璋修建南京城正愁着银根吃紧呢,当即责令他承包城墙三分之一的建筑工程。结果,他“抓了个棒槌就当针”,修过城墙之后,竟然异想天开,要拨出巨款去犒赏三军。这下子惹翻了那个杀人成瘾的朱皇帝,当即下令:“匹夫犒天子之军,乱民也。宜诛之!”亏得马皇后婉转说情,才算免遭刑戮,发配到云南瘴疠之地,最后客死他乡,闹得个人财两空。此中奥蕴多多,一一彰显在“无字书”里,关键在于后人能否解读出来。
如果说,这个堪笑又堪怜的悲剧角色还留得一点历史痕迹的话,那就是周庄街头随处可见的名为“万三蹄”的红烧猪蹄膀。这是当年沈万三大摆宴席的当家菜。据说,有一天,朱元璋带着亲信到他家里来作客,他受宠若惊,一时竟不知用什么珍馐美味招待是好。恰巧,这时膳房里飘出一股浓的肉香味,皇帝问他是什么佳肴,他便让厨师把炖得皮鲜肉嫩、汤色酱红、肥嘟嘟、软颤颤的猪蹄膀端了上来,随手从蹄膀下侧抽出一根刀样的细骨,轻盈地划了几下,皮肉便自然剖开。朱皇帝见了馋涎欲滴,一面大快朵颐,一面连声称赞:这“万三蹄”真是好。从此,这道沈家名菜便誉满了江南。
无独有偶。“万三蹄”之外,周庄还有一种列入江南三大名菜的“莼菜脍鲈羹”,它也同样联结着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西晋文学家张翰,尽管和异代同乡“沈大腕儿”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喝的是同一太湖的水,但他却是典型的潇洒出尘、任情适性的魏晋风度。史载,一天他正在河边闲步,忽然听到行船里有人弹琴,便立即登船拜访,结果,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大相钦悦”。许是像俞伯牙与钟子期那样以旷世知音相许吧,最后他竟随船而去,而未及告知家人。到了洛阳,被任命为大司马东曹掾。后来,他因眼见朝政腐败,天下大乱,为了全身远祸,遂于秋风乍起之时,托言思念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而买棹东归。朝廷因其擅离职守,予以除名,他也并不在乎。他说,人生贵在遂意适志,怎能羁身数千里外,以贪求名位、迷恋爵禄呢!后人因以“莼鲈之思”来表述思乡怀土之情。
三
如果说,读“无字书”——社会调查也好,出外旅行也好,对一般人来说,有利于丰富人生阅历,获取活的知识,开阔眼界,增益见闻;那么,对于一个以认知社会、剖析自我、解悟人生为职志的作家,还有更现实、更直捷的收获,那就是在读“无字书”的同时,有效地丰富了表现素材,促成了创作构思。
20世纪末,我有中州之行,访问了开封、洛阳和邯郸这三座历史名都,回来后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组散文。这些在历史上曾经繁华绮丽的文化名城,历经沧桑嬗变,当年胜迹早已荡然无存,但在故都遗址上,却还存有沉甸甸的文化积淀和历史记忆。漫步其间,我脑子里涌现出很多诗文经史,翻腾着春秋战国以来大部中华文明史的烟云。我写这些散文,没有停留于记叙曾经发生过的史事(尽管这也是颇有教益的),而是努力揭示对于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
“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三百多年的宋王朝留在故都开封的是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更是一面文化的回音壁,是诗人们从中打捞出来的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是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探寻。邯郸古道上,既有燕赵悲歌,也有黄粱幻梦,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意旨,竟能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和谐地汇聚在一起,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悠远的中国文化深入探究的兴趣。
通过凭吊洛阳的魏晋故城遗址,我写了废墟——这悲剧的文化,历史的读本,着眼点在于阐释文学的代价及其永恒价值。魏晋时期留给后人可供咀嚼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另一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思想十分活跃。一时学者、文人辈出,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敢于荡检逾闲,抒发真情实感,创作了许多辉耀千古的名篇佳作;尤其是他们所造就的诗性人生与魏晋风度,给予未来的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放浪形骸,任情适性,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代诗人赵翼的这一名句,既反映了文学创作规律,更揭示了时代塑造伟大作家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近年,我有机会重访江苏,曾有常熟古里之行。改变了那种随走随看的形式,我索性就把景观游览直接当作一部书卷来展读。在我看来,书香是古里的灵魂,是这座千年古镇的主题词,而诗卷则是它的展现方式。这样,我就借用古代画卷分为引首、卷本、拖尾的说法,写了一篇别开生面的游记,题目就叫《客子光阴诗卷里》。
首先入眼的是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于是,我把它作为诗卷的“引首”。踏在润滑的苔痕上,似乎走进了时间深处,生发出一种时空错位的神秘感觉,说不定哪扇门“吱呀”一开,迎面会碰上一个状元、进士。粉墙黛瓦中,一种以书为主体的竹简、雕版、抄本这些中国数千年文明进程中的文化符号,让他乡客子亲炙了瞿家五代在藏书、读书、护书、刻书、献书中所辉映的高贵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守望,体味到高华、隽永的书香文脉。那么,这部手卷的“卷本”在哪里呢?那就是凸显历史名镇、江南水乡、时代文明三大主题的文化公园。堪资令人欣慰的是,当年那种文脉、书香,今天得到了有效的弘扬,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如果说,铁琴铜剑楼这个“引首”是一篇阳春白雪的古体格律诗,那么,作为“卷本”的文化公园,则是一首现代自由体诗章。它集休闲、娱乐、学习、观赏、活动、展示等功能于一体,充分体现出时代化、大众化、人性化的特点。而异彩纷呈的波司登羽绒服工业园,则相当于整幅诗卷的“拖尾”。人们在这里,通过展馆接近实际的亮丽的风景线,形象地了解到这一世界著名品牌的奋斗历程和辉煌业绩,感受到融现代化工业色彩与文化韵味于一体的时尚旅游的真髓。
书香古镇孕育、滋养了万千读书种子,而这些读书种子,又以其超人才智和非凡业绩,反转过来为古镇跨越式发展创造出不竭资源。波司登的创建与发展,便是显著的一例。他们由过去靠推销人员“千山万水、千言万语”,跑遍全国各地去卖产品,转换为靠名牌的影响力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吸引世界客商走进来;企业从过去的单纯生产型转换为创意服务型,形成富有诗性的全新生态和源源不竭的动力,从而达致最高发展目标,称雄世界,独执亚洲羽绒服生产之牛耳。
同样是展读“无字书”,若是把在同里、周庄旅行看作是读史书,那在古里,则是在披览史迹的同时,又读到了许多粉墨淋漓、芸香扑鼻的现代作品。当然,即使是不久前发生的阅读情事,待到我执笔叙述的时节,它们也都像王右军在《兰亭序》中所说的,“向之所欣,俛仰之间,已为陈迹”。而这类历史的叙述,总是一种追溯性的认识,是从事后着手,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因而不能回避也无法拒绝笔者对于历史的当下阐释。就是说,作为“无字书”的解读者(同时也是叙述者),我总会通过当下的解读而印上个人思考的轨迹,留下一己剪裁、选择、判断的凿痕。——这同解读“有字书”,是原无二致的。
来源:《光明日报》( 2016年02月2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