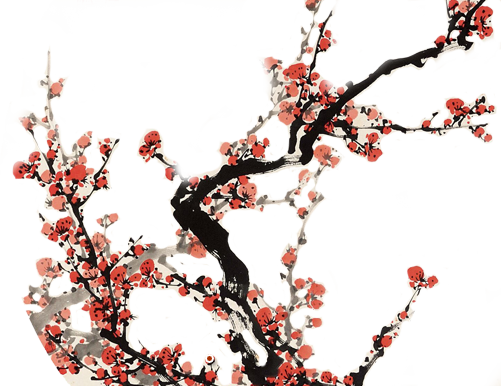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我的文学梦与现实同构”——王充闾答《充闾文集》编辑问
核心提示
《充闾文集》出版之际,作者王充闾与该文集责任编辑王亦言进行对话,他就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历史散文的创作初衷与灵感来源、如何平衡官员与文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好散文”标准、古体诗创作以及今后的创作打算回答了编辑问。
创作灵感与原动力都来自丰富多彩的现实
编辑:这次《充闾文集》的出版,收录了您的文学自传,您谈到了儿时读私塾和后来接受现代教育的大量经历与细节,而作为您后来走向文学创作的辉煌,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哪一方面对您的影响更大一些呢?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譬如建筑,二者是基础与本体的关系,它们对于文学创作的支撑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如果硬是以“哪个影响更大”的语式来表述,还得说是现代教育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更为鲜明、更为广泛,也更加直接,它所经历的时间也最长。当然,对于身在中国的作家、学者来说,若要不断创新、高张胜帜、拥有强大后劲,传统教育绝对不容忽视。有人以“童子功”来概括,其实它的作用远不止这一方面,它是基础中的基础,对于一个作家、学者来说,是终身起作用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讲究学兼中外、会通古今,所谓以圆览之功收会通之效。具有传统文化与国学的雄厚功底,对于一个作家、特别是学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编辑:您潜心治学、精心创作,同时也留心世务、关注现实,您本人和作品都具有让人清醒、冷静的力量。特别是读您的历史散文,总能让人清晰地看到对现实的观照。那么,您创作历史散文的初衷或者说是灵感来自于哪里?
王:我的文学之梦是与现实同构的。可以说,创作的灵感与原动力,包括想象力、创造力,全都来源于丰富多彩的现实。人民的事业,伟大的改革、建设,是文学艺术的不竭源泉。2009年,我在北大中文系《关于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期待》的演讲中,集中谈了这个问题。我谈到,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应,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将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人生际遇、命运抉择中的种种疑难、困惑表现出来,用过去鉴戒当下,寻找精神出路,这可以说是我写作历史散文的出发点。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个人的行藏、际遇、身世上,有的依托于浓烈的家国情怀,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抒怀寄慨,宣泄一己的感喟与见解。
我的历史文化散文形成多个系列,像帝王系列、文士系列、女性系列、友情系列、爱情系列,等等。而每个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摆浮搁”式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思想意蕴的步步延伸、层层递进、逐步深化。比如,我写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命运颠折,没有停止在对本人个性、气质的探求上,而是通过不同的篇章,从更深的层面上挖掘社会、体制方面的种因。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活着的人的灵魂拷问。每个读者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审视、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与轻松了。
编辑:您曾身为官员,但是与您接触之后,我们发现在您身上体现更多的是文人气质,请问您是如何平衡官员与文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的?
王:虽然过去我也曾久历官场,但从个性特征来说,我始终未脱文人习性、书生本色。当官也好,从政也好,无论进到哪一级,从本质上说,我还是个文人。像奶牛天生就是产奶的,文人无论在何等境遇下,总废弃不了读书、创作、治学。几十年间,出版了近50部散文随笔和诗词集,大多是业余时间的产物。工作担子很重,每天政务倥偬,百端丛集,除去“三餐一梦”,几乎抽不出时间读书,遑论创作、讲学!为此,我对时间作了严格的划分,八小时之内全身心地处理公务,绝不旁骛;业余时间、节假日,便沉浸在那片心灵的绿洲里,保持着心境的洁净与宁静,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搞创作。我珍惜每分每刻,努力避开各种世俗应酬和摒绝声色之娱。即使凌晨几十分钟的散步,也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凝想;甚至坐车出行,我也要带上一本书,一路上不停地看,不停地思考。连睡觉之前洗脚,双脚插在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本浏览,文友们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我很愿意与不同年龄段、不同学科、不同个性的文友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天南海北,学术界、作家群、教育界、出版界中,有许许多多倾心相与的朋友,这对于保持一种云水襟怀、书生本色,大有益处。
好散文既是一种精神创造又是一种文化积累
编辑:近年来,大众阅读趋向“散文热”,名列畅销书榜前茅的图书绝大部分是散文作品,而且偏重“心灵鸡汤”“励志”,更有许多关注女性情感的“小妞文学”。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是否是“好散文”,也在文学圈内不断引起热烈的讨论。请您从多年来从事散文创作的角度来谈一谈,如何判断一篇散文是不是“好”。
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由于每个作家所持标准不尽相同,很难做出划一的结论。这里只能说说一己之见。我心目中的好散文,应该具备审美的本质、情感的灌注、智慧的沉潜、意蕴的渗透,有识、有情、有文采、有意境,具备诗性的话语方式和深刻的心灵体验、生命体验,体现主体性、内倾性、个性化这些散文文体特征;既是一种精神的创造,又是一种文化的积累。文学在充分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应该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发掘,本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生存价值的深度关怀,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叩问、灵魂的对接,因此要从人性的角度深入发掘,具备深刻的心灵体验与生命体验,而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生活体验。表现在具体写作中,或者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抒写自己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厨川白村式的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或以匠心独运的功力,展示已经隐入历史帷幕后面的世事沧桑,以崭新的视角予以解读;或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和世俗语言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或经由冥思苦想、艺术的炼化和宗教式的参悟,将智性与神性交融互渗,使疲惫的灵魂遐想渺远的彼岸。
编辑:在《充闾文集》中收录了您的古体诗集,这也许与您在少年时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有着很大的关联。当下,许多古体诗作者抱怨缺少相对完备的自然环境和学习条件,影响创作的美感。在后现代的今天,古体诗创作的未来有怎样的愿景?它的生命力能否在新的人文环境中焕发?
王: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当前大体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简言之,分乐观与悲观两派。持乐观论者,满足于眼前古体诗词创作的轰轰烈烈,队伍庞大,数量山积,认为今后发展将成取代新诗之势; 悲观论者则恰恰相反,对于古体诗的前景并不看好。我是写古体诗的,也可以说,熟练地掌握了它的创作手法与规律;而对于新诗,则从未涉足,也并不怎么欣赏。这样说来,我似乎是支持古体诗的了。不,正由于我太懂得与热爱古体诗了,因而深知它的难处、它的困境,或者说无法摆脱的末路。闻一多先生说,诗到唐时尽。意思是今天已经不可能再有好的古体诗了。这话有些绝对以至武断——不要说宋代以至清代,就连晚清、民国年间也还有大量优秀古体诗人;但不能说此言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时移世异,环境、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仅缺少那样潜心创作、刻意推敲、具备深厚学养与灵思妙悟的出色诗人,而且也没有那样的读者群了。试想,在后现代的今天,身处“读图时代”,面对浮躁氛围,莫说是古体诗,连真气弥满、意蕴充盈的散文和小说都难得有人欣赏。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并非诗的时代,至于古体诗就更难说了。现在,铺天盖地的古体诗,数量确实可观,但质量却没有跟上去,许多只是勉强凑韵,了无诗味,不过是自娱自乐而已,令人不敢恭维。
计划围绕国学经典和古代学术大师写些文学随笔
编辑:您可否谈谈今后的创作、研究打算?
王:关于我的文学创作,有的知名学者提出“系统工程”的论断。不过,就我几十年创作历程的实际观察,许多作品的产生,事先并没有统一擘划,往往是随机出现的。比如那部代表性著作《逍遥游——庄子传》,就是2012年接受一项重要创作任务的产物——当然是在多年学术积累之上产生的,否则也难以完成。也许,今后还会有类似情况。事实上,一般性的文学作品,不同于学术著作,也很难事先有一个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的统筹规划。过去衡文,有“文章自古无凭据”的说法,作文何尝不是如此!兴之所至,灵感袭来;或者担子压肩,集中突围;或者“重贾余勇,再作冯妇”,都是常有的事。当然,计划中的写作与研究还是有的,比如,我就想围绕国学经典和古代学术大师写些文学随笔,像文集中所收录的写《周易》的《生生之谓易》,写孟子的《遗编一读想风标》等。这样,在20卷之后,每一两年还可望再推出一卷,接续地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