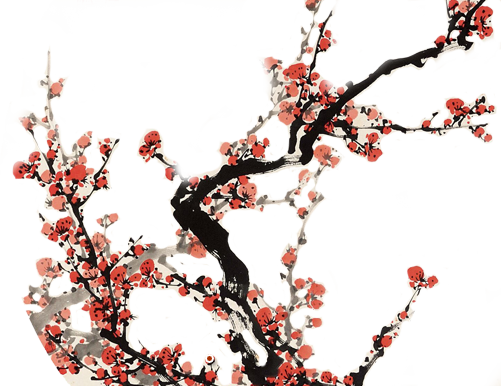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时代之光与民族之魂
——读王充闾散文有感
李秀文
《文在兹》系当代文学家、冰心散文奖获得者王充闾的散文精选。作者以其独到的视角审视、思考、探索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有着一定意义的历史文化现象,他的作品文笔优雅从容,意蕴精深幽远,流淌着其间的是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笔功底,文采诗意洋溢笔端。王充闾将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人性深处。以现代意识进行文化与人性的双重关照,它显示了作家凝望历史的现代眼光和以文学的视角掌控、表现历史。
一、情深意笃
王充闾当过教师、编辑乃至高官的丰富人生阅历,足迹曾遍及华夏欧美,遍访先贤胜地。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王充闾这里汇集为不断奔涌的文学源泉。他的深厚和独特,使他在20多年来散文创作整体格局中,不在潮流之中却在潮头之上。
王充闾的散文中,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深意笃倾向,不仅体现在他书写对象的选择上,同时也表现在他的修辞和表达方式上。他的游记名篇《清风白水》、《春宽梦窄》、《读三峡》、《山不在高》、《祁连雪》、《天上黄昏》、《情注河汾》、《神话的失踪》等,既有名满天下的名山大川风光胜地,也有僻陋孤山和闲情偶记。在这些散文中,他不只是状写风光的俊美旖旎或威严沧桑,而是更多地和个体心灵建立起联系。在红尘十丈的闹市喧嚣中,只有这些已“成追忆”的风光美景,才能让他心静如水并幻化为一片净土。或者说作家对这些纯净之地的心向往之,背后隐含的恰恰是他对纷乱世界和名利欲望的厌恶和不屑。一个作家书写的对象就是他关注和向往的对象。王充闾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正是他“跌入宦海”“误落尘网”的时候,但他似乎没有“千古文人侠客梦”,兼善天下为万世开太平的勃勃雄心。他似乎总是心有旁骛志不在此。传统文论强调“文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这里讲的是文章之学,而非文学之学。在曹丕看来,文章要以国家社稷为重,否则就是雕虫小技。但文学并不一定或者有能力担当如此重负。文学更多地还是与个人体验、禀赋、情怀、趣味相关。它要处理的是人类的精神事务,它的作用是渐进、缓慢地浸润世道人心。王充闾的风光游记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他在那一时代对文学的理解,但也似乎从一个方面左证了他对淡泊和宁静的情有独衷。因此,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作家对栖息心灵净土的一种寻找,当然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性策略。
我们注意到,王充闾在壮写这些对象的时候,以诗入景是他常用的艺术手法。这既与他的修养有关,也与他的情怀有关。但他以诗入景或以诗入画(风景如画),不是抒思古之幽情,发逝者之感慨,而是情境交融自然天成,无斧凿痕迹和迂腐气。这种手法超越的是“诗骚传统”,而凸现的则是书卷气息。“诗骚传统”始于话本小说,这一文学体式因多述勾栏瓦舍卖浆者流,四部不列士人不齿。为了表现它的有文化和儒雅气,故文中多有“有诗为证”。但王充闾的散文以诗入文却远远地超越了这一传统。《清风白水》是写九寨沟的游记,他起文便谈诗词,以“豪放”“婉约”形容风景的别样风格。泰山威严西湖如娥,但在王充闾的视野里,
九寨沟似乎与豪放婉约无关,它“是少男少女般的活泼、烂漫、清风白水,一片童真。”文章切入于名词佳句,却又与词义无关,豪放婉约在这里仅仅成了他的一种参照和比较。《春宽梦窄》起句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磅礴气势与飞秦岭越关山奔向西域的漫漫长途和心中激荡的豪情相得益彰。库尔勒作为古代边地,不能不使作家遥想当年,于是南宋词人姜夔在咏叹金兵压境、合肥几近边城的词句“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等句便油然而生。在《青天一缕霞》中,由呼兰河而萧红,由萧红联想到聂绀弩的“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的诗。这样的表现手法在王充闾的游记散文中几乎随处可见。但这些借用却使文章充满了浓烈的书卷气息,强烈地表现了作家对“美文”的追求和唯美主义的美学倾向。当然,“美文”不止是作家对修辞的讲求,更重要的是作家在文中体现出的情怀和趣味。即便是借用古典诗词,以诗词入文,王充闾整体表达出的风格是静穆幽远。他不偏婉约爱豪放,兼蓄并收为我所用,中和之风文如其人。行文儒雅内敛而不肆张扬,但他孜孜以求的不倦和坚韧,展示的却是他宠辱不惊镇定自若的风范和情怀。他对湖光山色的情趣,不是相忘于江湖的了却,而是对“天生丽质”纯净之地发自内心的一种亲和。
二、眼界深邃
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历史是一个永远感兴趣又永远说不尽的领域。这当然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有关。无论人生或治国,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总是试图在窥见历史的同时能照亮未来的道路。大概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进入90年代以后,所谓文化历史散文脱颖而出,在散文的困境中拓展出一条宽广大道。但同样是文化散文或历史散文,它们背后隐含的诉求是大异其趣的。我对那种动辄民族国家潸然泪下的单调煽情向来不以为然。但王充闾在他的文化历史散文中所表达的那种检讨、反省和有所皈依的诚实体会,则深怀信任。
就个人兴趣而言,王充闾似乎更钟情于淡泊宁静的精神生活。这不仅可以在他的创作自述《渴望超越》和明志式的散文《收拾雄心归淡泊》、《从容品味》、《华发回头认本根》中得到证实,而且在他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创作中表达得更为明确。他有一篇重要的作品:《用破一生心》。文章以曾国藩为对象,对曾的一生以简约却是准确的笔墨予以概括。这位“中兴第一名臣”的一生历来褒贬不一。但在王充闾看来,“这位曾公似乎并不象某些人说的那样可亲、可敬,倒是十足地可怜。他的生命乐章太不浏亮,在那淡漠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猥猥琐琐、畏畏缩缩的躯壳之外,看不到一丝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人们不仅要问上一句:活得那么苦,那么累,值得吗?”按说,曾国藩既通过“登龙入室,建立赫赫战功”达到了出人头地;又“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达到了名垂万世。他不仅是满清建国以来汉族大臣勋、权势、地位,无出其右者,而且在学术造诣上的精深也“冠冕一代”。因此也难怪有人对这“古今完人”的推崇和尊崇。但是,在曾国藩辉煌灿烂的人生背后,却掩埋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不仅官场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是与夫人私房玩笑也要检讨“闺房失敬”。如此分裂的人格在王充闾的笔下被揭示的淋漓尽致。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曾氏言行、表里的分裂和对人生目标期待的问题。虚伪和不真实构成了曾氏人生的另一个方面,而一个“苦”字则最深刻地概括了“中堂大人”的一生:“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现实人生中的一种欲望。”文中对曾氏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分裂的性格充满了不屑,但也充满了同情,他不是简单的批判和否定,同时也对人的历史局限性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他曾分析说:“雄厚而沉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为他作好了精确的设计,给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作别样的选择。他在读解历史认知时代的过程
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结构了,最终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制成品。于是,他本人也就像历史和时代那样复杂,那样诡谲,那样充满了悖论。这样一来,他也就作为父、祖辈道德观念的‘人质’,作为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彻底告别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无法摆脱其悲剧性的人生命运。”(《用破一生心》)
王充闾的《一夜芳邻》表达了相似的情感取向。勃朗特三姐妹的才华蜚声世界文坛,她们的作品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一部分。但他们都英年早逝,最长的也只活了39岁。作家有机会到三姐妹多年生活的哈沃斯访问,参观了三姐妹纪念馆。面对三姐妹的故居和纪念馆,作家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夜不成寐。于是走在三姐妹曾经走过的石径上,作家的想象闪现为夜色如梦般的幻影:“在凄清的夜色里,如果凯瑟琳的幽灵确是返回了呼啸山庄,古代中国诗人哀吟的‘魂来风林清,魄返关塞黑’果真化为现实,那么,这寂寞山村也不至于独由这几支昏黄的灯盏来撑持暗夜的荒凉了。噢,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朦胧中仿佛看到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或三姐妹正握着纤细的羽笔在伏案疾书哩;甚至还产生了幻听,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咳嗽从楼上断续传来。霎时,心头漾起一股矜持之情和深深的敬意。”三姐妹的生活贫病交加,寂寞凄苦。她们离群索居却早早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牧师父亲的教育影响下有了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表现力。她们创作了不朽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她们都有一颗金子般闪亮的心。作家动情地写到:“在一个个寂寞的白天和不眠之夜,她们挺着病痛,伴着孤独,咀嚼着回忆与憧憬的凄清、隽永。她们傲骨嶙峋地冷对着权势,极端憎恶上流社会的虚伪与残暴;而内心里却炽燃着盈盈爱意与似水柔情,深深地同情着一切不幸的人。”如果说易安居士的性格是内敛的,更关注个人内心的体验,那么,三姐妹的心灵则是开放的,她们把同情和爱更多地给予了并没有太多直接经验的不幸的人们。这种高贵的内心洋溢着宗教般的温暖和撼人心魄的诗意。对这些经典作家灵魂的旁白或独语,其实也是作家自己生命感悟或心灵体验的自述。他曾有过这样的自我诠释:“所谓生命体验与心灵体验,依我看,是指人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特定情况下,处于某种典型的、不可解脱和改变的境遇之中,以至达到极致状态,使自身为其所化、所创造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情感经历。它的内涵极为丰富,而且有巨大的涵盖性。它主要是指写作者自身而言,也包括作家对于关照对象在精神层面上的心灵体验,包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实际体验。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渴望超越》)
王充闾在历史隧道中对历史人物的想象和相遇,作家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美学趣味获得了检视。如果说这类作品还是建立在个人兴趣或偏爱范畴内的话,那么,他的另一类历史散文则表达了他对历史重大事件的史家眼光和以文学的方式处理重大题材的能力。《土囊吟》、《文明的征服》、《叩问沧桑》、《黍离》、《麦秀》等作品,是对曾经沧桑的久远历史的再度审视,是对文明与代价的再度追问。对陈桥崖海、邯郸古道、魏晋故城、金元铁骑等的追忆中,在社会动乱、朝代更迭、诸家云起、狼烟风火的争斗和取代过程中,辨析了历史与文明的发展规律,识别了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特殊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土囊吟》和《文明的征服》,对一个强大和强悍民族统治失败的分析,不仅重现了历史教训,而且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它的现实意义尤为重大。一种文明无论出于主动的对另一种文明的向往,还是处于被动的无奈的被吞噬,都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解体或破产。文明的隐形规约和凝聚力是看不见的,但它又无处不在。这些作品,在真实的史实基础上,重在理性分析,在史传中发掘出与当下相关的重大意义。它显示了作家凝望历史的现代眼光和以文学的视角掌控、表现历史的非凡功力,它的宏观性和纵横开阖的游刃有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作家丰富扎实的历史学修养和举重若轻的文学表现力。
三、朴素自然
探讨这一领域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从一个庞大的乌托邦框架出发,并没有提供一个普世性、终极的精神宿地。而是以相当个人化的方式,实现了他个人的精神还乡。这个精神故地,既是他亲历生长的地方,也是一个遥远但却日益清晰的梦乡。王充闾有一本散文集,他将其命名为《何处是归程》。这个命名隐含了一种沧桑、悲凉和困顿,同时也隐含了一种叩问和探询的坚忍。书前有两首七绝题记诗。其一:“世间无缆系流光,今古词人引憾长。且赏飞花存碎影,勉从腕底感苍凉。”其二:“生涯旅寄等飘蓬,浮世嚣烦百感增。为雨为晴浑不觉,小窗心语觅归程。”诗中确有对人生短暂苍凉的慨叹和难以名状的悲剧意识。但这种悲剧并不仅仅源于“无缆系流光”的无奈,它更来自诗人对“浮世嚣烦”,世人对功名利禄的争斗或倾轧。特别是诗人“人过中年”之后,似乎就有打点心灵归程的意思了。
但王充闾的这一努力的价值就在于,在这个困顿迷茫心灵家园成为问题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执意追寻的勇气,表现出了对“现代性”两面性认识的自觉。当然,“精神还乡”仅仅是一个表意符号,没有人会认为王充闾要退回到“前现代”或乡村牧歌时代。那个只可想象而不可重临的乡村乌托邦,在王充闾的反省中已经解决。他的这一追求背后隐含的是他对精神困境的焦虑和突围的强烈愿望。在物资世界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时代,在世俗生活的合法性得到了确立之后,人如何解决心灵归属的问题便日益迫切。王充闾只不过以“精神还乡”的方式表达了他解决精神归属的意愿而不是最后的答案。重要的是,对不同领域写作的开拓,一方面显示了王充闾开放的心态,他愿意并试图在不同的领地一试身手,将“关已”的灵魂问题提出,一方面,也展示了他在创作上“螺旋式”前进的步履。他没有将自己限定在所谓的“风格”领域,一条道走到黑。而总是在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中别有新声。这个现象是尤为引人瞩目的。这时,我想起了他最近的一篇命名为《驯心》的文章。文中对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驯化,或福柯所说的“规训”,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传统文化对士人的驯心,在于让这个阶层的价值尺度永远停留在一个方位和目标上,在于让他们永远失去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就像“熬鹰”一样,让志在千里的雄鹰乖乖就范。王充闾曾在官场,也生活于世界即商场的时代,但他仍然没有被“驯心”。他独立的思想和情怀,在温和从容的书写中恰恰表现出了一种铮铮傲骨,在貌似散淡的述说中坚持了一种文化信念。这是王充闾散文获得普遍赞誉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他能在散文的困境中矗起一座丰碑的真正原因。
充闾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的第六本诗集《弯弯的月亮》就是他题写书名的。当我在省作代会提出这个要求时他欣然接受并很快地写好寄给我。这一印象之深刻几乎不能忘记。你可以把他理解为一位学富五车的教授,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者,就是难以和权高位重的高官联系起来。读了他不断求索、独步文坛的大量散文创作之后,我多少迷惑的心情终于豁然:正是他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文章。这就是:“文如其人”。相信王充闾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时代,奉献给家乡和人民。(作者为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