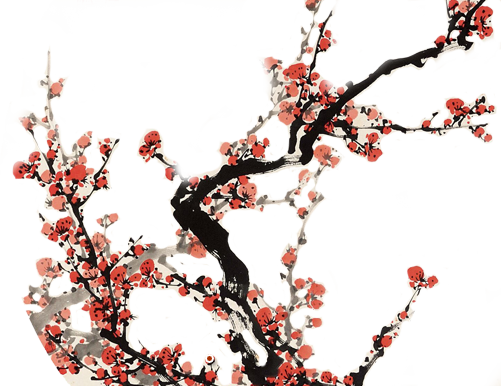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感悟于“自然”
---读王充闾先生《庄子全传》有感
郭玉杰
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都表现出了以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描写对象,主要人物和事件符合史实,而且人物生平经历具有相当的完整性。作者通过生动的情节叙述和语言描写,塑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从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并且感染读者。王充闾先生的《逍遥游·庄子全传》正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为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作全传,可想而知,难度之大。其一,史料匮乏,内容零散,正史记载聊聊,就连司马迁的《史记》也只是在《列传第三·老子 庄子 申不害 韩非》中数言略表。之后,虽历代传疏、研读的文章不断,但皆见仁见智,且大多只唯《庄子》一书探讨,难以形成庄子其人的完整性。其二,有关庄子的考古记录,几乎无影,造成庄子的生平经历除《庄子》和有关史料的散记之外,大多是传说。然而,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王充闾先生竟历经十余载,成就“一部全面而详尽的《庄子全传》”,全书生动形象又不乏学术品味,具有文史哲兼备、雅俗共赏、古今贯通的特质。作者以严谨的写作态度,依据《庄子》文本及相关史料、传说,汲取融合历代贤哲的众多研究成果,经过精心组织材料,巧妙布局谋篇,以散文形式、写实手法,呈现了庄子的生命历程、生活状态、人生特征、思想轨迹,彰显了庄子的影响力,完成了“时代巨人”——庄子的形象塑造,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优良文化传统的传承,贯注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拜读此书,如曲径通幽,时而山重水复,时而柳暗花明。虽感触颇多且益深,却只能谈浅点滴之得。
王充闾先生以严谨遵奉史实的态度,旁征博引,揭去了庄子两千余年来扑朔迷离,甚至神秘莫测的面纱,为读者写出了一位呼之欲出、可感可近的“庄老先生”。《庄子全传》叙事娓娓道来,语言瑰丽而不失朴实,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读者都会有不同程度、各得其所的收益。青年人读之,会感悟到庄子着眼于精神自由、崇尚思想解放的逍遥;中年人读之,会领悟到庄子摆脱功名利禄,鄙视金钱权力的超越。因为“庄子哲学是艰难时世的产物,体现了应对乱世、浊世、衰世的生命智慧。”庄子面对战国纷争的现实,不做所谓的真“隐士”。王充闾先生曾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隐士》中说,“古代士人的隐心,分自觉与被动两途,有些人是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磨损胸中万古刀’,逐步收心敛性,实现对传统人格范式的超越。也有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为旨归,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不‘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价值观,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庄子自然是后者,而且以此心观其世,又以“游世”之行而对之。于是他不逃避现实,也不做进攻者,更无战胜之意,而是坚守自然本性,维护生命自由,在夹缝中生存,在乱世、浊世、衰世中摆脱困境,养性全生。此种人生之道,对后世而言,即使人们生活的时代不是乱世、浊世、衰世,但世间的各种矛盾与纷争也是层出不穷与变化多端的,同样值得人们思考、借鉴、吸取,从庄子身上得到启示。
感触尤深者是老年人读《庄子全传》,若结合自身生活阅历,细细咀嚼,更应受益匪浅。老年人经历多,尤其是曾入世多年者,遍察人事;一经出世,更应转换思维方式和生活样式。若想从从繁杂中解脱出来,走向简单,面对世事“想得开”“放得下”,颐养天年;阅读感悟《庄子全传》,则会事半功倍。
《庄子全传》一书在庄子之“自然观”方面,突出了“回归自然本真,重视生命个体”这一点,并为人们作了明了的解析。“自然”是庄子在《庄子》一书中反复阐述的核心理念,更是他一生探求与追求的极致。王充闾先生在《庄子全传》中为人们作了深刻而明晰的解释:“崇尚自然,回归自然,顺应自然,这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这个‘自然’应该是广义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盖自然境界,并具有本性、本然、本根的内蕴。”人们本自置身于自然界,可是面对的却是大量的“人化的自然”。这样,就应该选择好并进入到一种适合自我、不碍他人的“自然境界”。这种“自然境界”表现在如何对待人世、事物的方方面面,而庄子的“崇尚、回归、顺应”,特别是“顺应”,便是足可借鉴、可取的途径。
人之暮年,虽寡事清为,但有人仍会有萦萦于怀、挥之不去的自忧,很难找到一种“娱我”且“忘我”的“自然境界”。人人难以逾越的生老病死的“死”,令多少人思之如虎、闻之若狼。如果能从《庄子全传》中有关庄子生死观的叙述与阐释中得其一二,则会渐渐明白。王充闾先生在《庄子全传》第五章第十七节“哲人其萎”中这样写到,庄子的生死观就是“生寄死归”,生死一如。生命只是偶然的有限的历程,生是死前的一段过程,活着时宛如住在旅馆,死去就是回家了;生与死不过是一种形态的变化,生死是同一的,同归于“道”这个本体。
这个“道”即自然,生死同一,皆属自然。此在《庄子·至乐》篇“鼓盆而歌”中可证:“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慨)!然察其始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自以为不通乎命”的“命”,便是自然。
这样的生死观不但表现于别人,就是于其本人,也如此。在《庄子·列御寇》篇记之:“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更有史料佐之,《意林》引桓谭《新论》载:“庄周病剧,弟子对泣之。应曰:‘我今死则谁先?更百年生则谁后?必不得免,何贪于须臾。’”死是归于自然,有“天地”“日月”“星辰”“万物”为“葬具”,何须“加”。“乌鸢”“蝼蚁”皆属自然,何必“偏”。“谁先”“谁后”都不可避免,为何贪于片刻。
如此纪实的文字,如此平静地对待死亡,可见庄子之生死观的豁达,自然中存在生命,生命中包含生死,生死是自然之事,于是顺应自然,以理化情。其死即“回归”,自可“顺应”,归结为,是其对自然的本真的“崇尚”。这种“崇尚”使人从诸多束缚中解脱出来,进而达到了身心的自由与超越。
庄子面对“死生亦大矣”的“死”能如此“自然”“逍遥”,回溯其一生,辞去“漆园吏”“宁其生而曵尾于涂中”,不做“牺牛”而可得为“孤豚”,甘为“泽雉”等等,皆显现了其特立独行又远见超凡的清醒;于是“游世”生存,安贫乐道,传道、授业、解惑。庄子如此清醒的根本源于“道”,虽然庄子之“道”始于老子之“道”,但对老子之“道”有批判式的继承和创造性的发展,体现了他“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思想。“道”是可言、可议、可见、可听、可触的,“道”是无处不在且现身于具体事物之中的,“道”是与人生思考、生命纵谈、精神自由、思想解放相融的,他使“道”更加丰满而具体;于是成其为“庄子之道”。王充闾先生把“庄子之道”解析为五张面孔,使读者更清晰地认识了“庄子之道”。其第二张面孔即“庄子之道”“表现为自然性”,而且将其“自然性”从人之个体的“生死观”拓展到时世的“生存观”的大视野。王充闾先生这样认为,“庄子极力反对短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否定人类出于功利目的,对自然进行种种干扰与破坏;认为物无贵贱,都有同样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他极度痛心地描绘了由于打乱自然秩序、背弃生物本性所造成的鸟惊兽窜,草木不得生长,昆虫无处栖身,万物失去生存环境的惨景,表达了他对于生态平衡的关切之情。”这是两千多年前庄子忧虑的目光与今人睿智的观察的碰撞与契合。面对我们的生存环境,人为地过度开发,已造成了生态的失衡,是该慎重地思考庄子的“自然观”了。人类中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阶层,无论哪个职业,无论哪个年龄,都应慎思于己,合理开发利用,则“人与天一”和谐发展,因为自然资源的“绿水青山”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金山银山”。
由于历史的局限,就“自然”而言,庄子的“自然观”自有偏见一面,王充闾先生在第十八节“身后衰荣”中指出,庄子主张一切顺应自然,不对自然进行人为的加工,批判人类粗暴地征服、控制、掠夺大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反对对大自然进行任何改变,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这也是一种偏颇。
《庄子全传》给人的益处既宽阔又深远,她立体化地让我们感知了“时代巨人”庄子及《庄子》一书的精华。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庄子用文字表现的是“警示”,而不同于儒家的“说教”,此点更值得深悟。庄子主张“与时俱化”,这也给我们以启示,对庄子的“自然观”只有借鉴、吸取,“化”为创新的“自我”;因为自然不可复制,自然境界更不可复制,一旦复制,则僵化,则异己;异己则泯灭了人格的自由、精神的独立和境界的超越。
(作者为学者、诗人,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