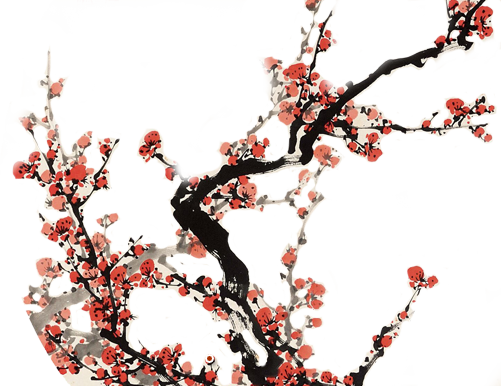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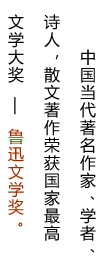

论王充闾散文中的历史意识
张 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得文化领域兴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浪潮,而开放的话语空间、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社会文化带来了某种浮躁气氛。作为对这种开放——浮躁的双重现状的写照与回应,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情智释放和对文化自我的重新确认,散文领域由余秋雨率先竖起了“文化散文”的大旗,一时应者云集,形成了二十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散文思潮之一:“文化散文”热。王充闾作为文化散文实践者之一,其创作以鲜明的风格独树一帜,赢得了广泛的欣赏和赞誉。文化散文作者们多习惯从历史典故中提炼富有文化意味的写作素材,从山水中印证古典词章中鲜活的人物故事,他们有一种“历史癖”,常常将一己的生命感悟投入敻远的历史时空,面对历史与人文风景,时而愤慨激昂,时而伤恸感怀,笔下交织着智性之光与感性之力。王充闾也不例外,他有着广博的人文历史知识的积淀,也有着深厚的古典诗文素养和独特的生命体悟,他的历史散文因而有着智性与诗性的双重色彩。在王充闾笔下,历史与现实是一种互为镜像的关系,是时间链条上不同的点,话语空间里并置的风景;他从山水与诗文中感悟历史,观照历史,获得了超越时空的诗性审美体验;而贯穿始终的则是他对于历史中的人的关怀,对人性话题的不懈探索。
一、散文家写史各有各的出发点,有的是借历史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这种散文表面写史,实质是借对历史的文化批判达到自我抒写的目的。如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一文中的“苏东坡”就带有作者很强的自我投影,出发点是对于个体生命的思考。一种是打通了历史与现实间的界限,借写史来抒发现实关怀,带有杂文式的针砭色彩,出发点是对于现实社会人生的关怀。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多属于后者。读王充闾散文的一个较深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散文家,他习惯从历史的比较、归纳、提升中得出一些普遍性的历史规律,借以针砭现实人生。他的散文的眼界是阔大的,这跟他的文化积淀和文化视野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对社会、人生有着普遍的担当意识和关怀意识。这种担当和关怀大多数时候并非直接的言说,而是通过对史料的裁剪、对历史的带有现实意味的阐述体现出的一种立场和姿态。像《用破一生心》《人生几度秋凉》《他这一辈子》等文,叙事占主体,没有太多的议论,但通过史料裁剪与适时抒情,我们自然能够读出作者鲜明的价值立场。
历史有着针砭现实的借鉴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常常被当作现实的一面镜子。在王充闾笔下,我们也不难发现类似的“借镜”的意图。如他所言:“离开了中国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现在,也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借鉴的意图可说是明显的。不过,现代人的散文,经过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在古典与正统之外也已染上了某种现代性的思维。这种思维用作者的话说是“用现实的观点看待历史,用历史的观点看待现实”,正说明了现实与历史是一种互为镜像的关系。
历史与现实互为镜像,这是王充闾散文中一贯的逻辑思维。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帝王也好,政客、文人也好,我们往往不觉其遥远,而好像是读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荣显、困顿与逍遥,作者有一种毫无距离感的、如在目前的把握。这不仅是因作者熟谙历史知识,还因他将自己的现实感悟渗透其中,做到了读历史就好像在读现实,打消了历史与现实之间那层时空的迷雾。历史与现实之所以能够互为镜像,很大程度在于这两者之间的相对性与相似性。什么是历史?什么又是现实?“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作者面对“陈桥崖海须臾事”的历史景观,发出了如此叹息。“今”与“昔”本是相对的,“今”总会变成“昔”,而“昔”曾经是“今”。没有什么是恒久永驻的,所谓的历史与现实,不过是我们方便计算时间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已。“古往今来,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交叉点,无论人们怎样冀求长久,渴望永恒,但相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却只能是电光石火一般的瞬息、须臾。”《陈桥崖海须臾事》这种对于时间的暂住性的体悟看上去是颇有古典式的感伤色彩的,而骨子里却已浸染了现代人的时间观念——如果说古典的时间意识是一种春去秋来的、回环往复的循环意识,现代人的时间意识则是线性的,时间链条上的每一点都转瞬即逝。“今”与“昔”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的,同时也是相似的。从历史的物化形态看,陈桥也好,濠梁也罢,以至严陵钓台、双溪春色,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所谓的“物是人非事事休”,但从时间上看,时间链条上的不同的点之间常常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如作者写到宋朝的开国与亡国,引用一诗“忆昔陈桥兵变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借对宋朝的开国与亡国两个时间点的特写,写尽了历史上兴亡盛衰的无常之慨,也写尽了那个“无常”背后必然的规律,从而发出了“这历史上惊人的相似之处,确是一个绝妙的讽刺”的感叹,让人对于现实社会、大千世界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警惕与理性的审视。
王充闾的散文常将现实与历史置于同一个话语空间里进行对话,大到时空场景,微至人物心理,都被发掘出了一种深刻的逻辑关联。而这里所说的“现实”未必是指我们的当下,“历史”也未必是“当下之前”。作者常常置身于某个过去的“现实”时段,再对照那以前的“历史”,挖掘出不同的时空里的共性与规律。如上文所说,现实与历史之所以能够互为镜像,是因为这两者常是相对而又相似的。“相对”是就同一条时间链条的无数的时间点而言的,“相似”说的是某些历史情节看上去的重复。还以《陈桥崖海须臾事》一文为例:宋王朝以“欺他寡妇与孤儿”夺得天下,又以“寡妇孤儿又被欺”落幕,这听起来有点历史循环论的味道。不过,如作者所说,“历史不能以‘循环’二字来概括,但它确实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确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的相似并不是重复,因为永远没有重复的历史,而只有重复出现的历史规律。
如果说,我们往常的历史观不过是将现在与过去区别开来,可以称作一种“小历史,是静止的、绝对的,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存在着一条泾渭分明的鸿沟,那么,在王充闾笔下则有一种浑融一气的历史意识,是一种“大历史观”,是将现实也纳入历史的范畴。
历史与现实总是处在特定的时空中的,一个作家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往往体现了他的时空观念,而时空观念说到底又是一种文化观念和价值认知的体现。诚如有论者所言:“积极开放的时空观念决定王充闾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着意进行现实的文化审视和灵魂拷问,而不仅仅将之视为一种创作题材,更不借此发思古之幽情。他总是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前提下,着重进行历史文化精神的开掘,关注历史人物,探索历史上文人的精神世界,弘扬民族传统精神,摈弃民族心理重负,重构民族文化精神始终是他创作的主旋律。”由此,我们可以说,王充闾的时空观念背后有着一个“心怀天下事,为国担忧”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也正因为他有着这样的胸怀和忧患,他才会如此有意识地“肩负着文化的重荷”,游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将不同时空里的人文风景并置在同一个话语空间里,以历史之镜映照现实,从现实之境阐释历史,带给我们一种时空交错、意味深长的感悟与启示。
二、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如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散文集《春宽梦窄》,已经显露出一种大气象,叙事、说理都显示了缜密的艺术匠心,但这些作品似乎还没有达到一个审美的高度,有时还带有杨朔散文时代的思维惯性,不免有些生硬。到后来的《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等集始显示出了审美上的飞跃,行文间不仅有了鲜活的作者自我生命性情的参与,那种叙事的张力和感染力也大大增强了。
如果说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符号,蕴涵了作者对于历史文化的感悟与思考,那么王充闾笔下的历史诗性常体现为一种语言的诗性。比如他喜欢在文章里使用文言词汇,特别是四字语的频繁出现使他的散文有一种古典的整饬,读上去有一种古文的节奏感。例如《青眼高歌》中写到纳兰性德:“是一个醉心风雅、酷爱生活而薄于功名利禄的人。虽然出身于豪门望族,却不愿意交结达官贵人,尤其看不起那些趋炎附势的‘热客’和饫甘餍肥、醉生梦死的纨绔子弟。”此类表达在王充闾散文中俯拾即是,不仅从字面上看,从节奏上读起来也颇古色古香。不可否认,较之同时代的许多散文家,王充闾散文里没有西化的语言、隐喻的句式,以及奇巧的叙事结构,他的散文总体来说是朴素的,很少故作惊人之语,但这种朴素里蕴含了旧式文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字素养,体现了一种源自文化典籍的古朴诗意。
对历史的诗性表述归根结底离不开作者自我意识的冲动,离不开作者从心理层面与历史人物发生的激情共鸣。如上所述,王充闾散文对于历史有一种毫无距离感的把握。这种零距离的历史把握最鲜明地体现在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剖析上。作者常用心理分析的手法去贴近人物的遭遇,让自己与历史人物发生某种生命的共鸣。如写《两个李白》,就深入到了李白的内心,揭示出了作为现实存在的李白和作为诗意存在的李白之间的内在冲突,将李白的狂放、志满乾坤的政治抱负展露无遗,细致描述了他在一次次政治挫折之后的苦痛、愤懑与孤独。作者这样描述李白:“他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旨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贤帝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这要寄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深刻揭示出了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作者接着又写了李白虽仕途困顿,壮志难酬,却偏偏留下了千古诗名——李白曾经的功名之想统统烟消云散在历史中,而惟独留下了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把“两个李白”之间产生的历史的讽刺、个体的悲剧、生命的荒诞都写得入木三分。同样的对于历史人物的心理剖析在《用破一生心》、《人生几度秋凉》中也有绝妙的展现。如写曾国藩:“作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家,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接受程朱理学巧伪、矫饰的同时,却能不为其迂腐和空疏所拘缚,表现出足够的成熟与圆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而他自己,时而日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表演意识”、“人格面具”二词可谓将曾国藩的人格与心理分析得丝丝入扣,颇见作者深邃冷峻的历史眼光,也可见作者强烈的爱憎褒贬和价值立场。
如果说通过剖析历史人物的遭际与内心世界,王充闾的散文达到了一种心理的深度,给人以情感共振的感性的诗美,那么通过对诗文典故的援引与阐释,我们则能看到一种源自文化经典,蕴具象于抽象的哲理美。
跟同时代的文化散文作者一样,王充闾喜爱名山大川,有一种“山水癖”,这种“山水癖”是对山水风物的热爱,尤其是对那些有着人文积淀的山水胜迹的热爱。而“山水癖”说到底又是一种“历史癖”和“诗文癖”——“外出旅游,寻访古迹,我常常是跟着诗文走”,作者在《桐波江上一丝风》一文中这样说过,说明了作者的山水之旅实为“诗文之旅”、“历史之旅”。这种将山水契合进历史文化中的思维惯性不独王充闾所有,山水本是自然,山水自然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身就具有文化积淀和文化意味,历来是文人发思古幽情的渊薮。某种意义上,王充闾笔下的山水只是一种话语背景和媒介,他感兴趣的毋宁是山水背后隐现的一段段的历史承载,是那种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时间暗示和沧桑意味。但从山水到历史,似乎并不一定有诗性的介入。因为原生态的山水是死的、静止的,而未经阐述的历史也只是故纸堆里的一堆堆发黄的记载而已。这时候,作者个人的记忆就参与了进来,因为历史的美感和山水的美感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美感,这种文化美感需要个体性情和个体审美的参与,只有融入了个体的记忆与感悟,山水与历史才能灵动起来,成为一种活生生的存在。当然,作者的记忆不可能是亲历历史的记忆,因为历史太遥远,但是作者有另一种形式的记忆,那就是对古典诗文的记忆。的确,“一切历史只能复活在回忆之中”(《陈桥崖海须臾事》),而这个回忆的触媒就是古典诗文。“桐波江上一丝风”、“陈桥崖海须臾事”、“夕阳红树照乌伤”、“寂寞濠梁过雨余”、“纳兰心事几曾知”……只要翻阅起那些有着特定所指的诗句,再对照着某一时映现眼前的山水胜迹,作者心中就油然而生一种恰如灵光遇合般的冲动,好像凭由那些山水遗迹和胸中的诗文记忆,他就突然与古人相逢在浩渺的时空中了,从而在心中翻涌起种种思量与感慨。这种感慨说到底是古往今来的文人面对浩渺时空,面对逝去与永恒所发出的感慨:“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站在历史的峰峦上登高远眺所获得的深沉的历史感,是一种超越今古时空、令人动心动容的多重感受……是情感的一次次升华,诗情的一次次跃动,哲思的一次次闪现”。除了以诗文记忆抒写对时空变幻、沧桑历史的感悟与认知,王充闾也经常在散文中穿插进自己的古体诗创作,发出一声声自我心灵的回响与震颤。于是在他的散文里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不仅诗文记忆与山水胜迹形成一种对话与诘问的关系,他自己的诗与古典诗文也形成一种对话和交流的关系。历史、山水、古人的诗与作者的诗在这里交融为一体,互相映衬,生发出一种诗的意境和美的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充闾不仅是一个散文家,更是一个从骨子里散发出才华与灵犀的诗人。
三、“诗性精神的实质是一种人文关怀。”王充闾的散文写历史,归根结底是写历史中的人,使用的是“人性扫描”的手法。所谓“人性扫描”就是把历史人物放到“人性”这枚放大镜下仔细观察,反复推敲。从人性的切入点而非从政治的、社会的切入点叙述历史人物。这意味着将历史人物当作真实的、血肉丰满的人而不是被神化、异化了的人来看待。
王充闾是一位有着浓厚的入世情怀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散文家,他是比较崇拜英雄的,但“英雄”二字仁者见仁。诚然,作者对历史上建立了世俗丰功伟业的人物是欣赏的。如对远至创建了后金的努尔哈赤,近至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他都有一种由衷地欣赏与看重。而更多时候,他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在他看来,有着一世功名的大人物也极可能是可怜与可悲的,而那些终身潦倒落魄之人却常散发着亘古的人格魅力与人性光芒。在不同的作品里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例子是曾国藩与大诗人陆游。以世俗的功名而论,作者承认曾国藩是“中兴第一名臣”,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声名煊赫的。但面对这样一个在历史上掀动了不少波澜、引发了不少话题的人物,作者却觉得其“不那么可亲、可敬,倒是有些可悲可怜。他的生命乐章很不嘹亮,在那巨大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猥琐、畏缩的躯壳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可谓做的是翻案文章,读来颇有些意外的惊喜。《用破一生心》写曾国藩的一生被“内圣外王”的欲求所紧紧捆缚着,欲进不得、欲退不舍,时时处处胆战心惊,永远戴着一副理学家的人格面具,虽居高位而如同身在炼狱,未免活得太累、太可怜了。曾国藩的人性是扭曲的人性,曾国藩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作者可说是撕去了大人物脸上的光辉面具,揭示了这个人物身上的矛盾性与悲剧性。读来痛快之余,也会被作者细致入微的人性洞察力所折服。如果说曾国藩是一个人性论意义上的悲剧,王充闾笔下的陆游则是一个世俗论意义上的悲剧。陆游的人生充满了失意与凄苦。从他动荡的爱情生活到坎坷的仕途,以及毕生难酬的爱国壮志,陆游可说是受尽了世俗的苦难,而只能从梦中去寻觅失意的爱情与功业。尽管陆游是一个世俗人生的失败者,作者却认为他仍不愧为一个“感情完整、境界高远的诗翁”因他是一个对爱情忠贞、对自我真诚、忧患苍生的人物,因为这种忠贞、真诚与忧患,陆游的诗也获得了高远的境界以致名垂千古,不啻为另一种成功。王充闾似乎特别青睐那些生平不甚得意,而充满了人性光辉的人物,类似的还有王勃、骆宾王、苏东坡、纳兰性德等。他们都是文人,而兼有为苍生、为天下的政治抱负,他们的仕途常常是困顿、波折、失意的,但他们又都有着真挚的诗人灵魂和高蹈的生命境界。由此可见,王充闾对历史人物所采取的是一种人性叙述的方式,他不大注重这些人建立了什么丰功伟业,而注意挖掘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挖掘他们世俗声名背后的真实人格和他们在各自生存困境中所表现出的人性姿态。换言之,对王充闾而言,一个个历史人物就好像一个个的人性宝藏,他寻觅着,追问着,也从中感悟着各式各样的人生遭际所带给他的充满人性启示的生命悸动。
王充闾的散文写历史有着人性的深度,这不仅表现为他能烛隐抉微,写出真实立体的历史人物,更在于他能够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态度,直击人性中的阴暗与丑陋,体现出一种对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坚守与追求。如《灵魂的拷问》一文写清代大学者陈梦雷被“知心朋友”李光地背叛、陷害的史实,读来有着沉甸甸的分量。跟作者的大多数散文不同,《灵魂的拷问》是不那么诗意敦厚的,而显出了几分辛辣尖锐。文章从陈梦雷的遭遇写起,直接联想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政治运动中的人性表现:“在所谓‘群体性的历史灾难’中,个人的卑劣人性往往被‘时代悲剧’、‘体制缺陷’等重重迷雾遮掩起来,致使大多数人更多地着眼于社会环境因素,而轻忽了、淡化了个人应负的道义责任”。“李光地”的人性丑陋和政治运动中某些知识分子的人性表演发生的背景不同,本质上却没有什么差别,都为我们揭示了同样的人性难题,也带给我们同样沉重的思考。作者对此显然很警醒,态度也很鲜明。他对“李光地”之流是深恶痛绝的,对“李光地”之流不但没有遭到应有报应反而得志终生表现出了一种困惑和愤懑。历史的悖论或许在于,善恶未必都有报,但面对这种悖论,作者并未表现出半点的妥协,而是勇于鞭挞,执着地坚守自己的价值立场,面对人性中的沉重面,他不愿意冷眼旁观,而愿意用整颗心灵去感受人性灾难,去品尝那份辛辣的人性拷问,去亲历那种无辜的人性煎熬。《灵魂的拷问》或许可称得上是王充闾散文里的极品,这篇散文是没有什么诗意的,但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抒写的维度,它对历史无意去做不痛不痒的戏说和无关紧要的粉饰,而是饱含了自我全部的理性与激情,如利刃般直切人性的腐烂之处,从感官到心灵,都让人有一种震颤。而行文的犀利之处让人想起鲁迅杂文的冷峻与决绝,寄语沉痛之处又有唐宋八大家“文以载道”的流风余韵。如果说“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那么在今天的语境中,散文已不再缺乏自由的话语空间,也不再缺乏对于人的复杂性的烛隐抉微的表现,而唯独缺少一种精神的向度和人性的高度,缺少的是直面人性困境和人性难题、既善于感悟人生又勇于承担人生的精神。而这或许是王充闾散文在当下语境中所保持的最为可贵的话语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