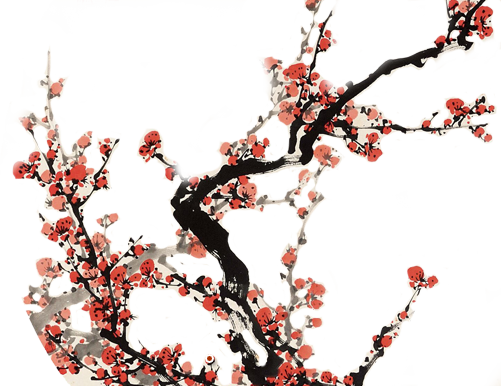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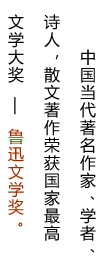

评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
颜翔林
新时期的历史文化散文场景,不能不关涉到王充闾及其文本。作家以一系列富有审美个性的散文作品,以美学的方式和历史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重新阐释历史和追问历史,合理想象历史和寻找历史之谜的解答,对历史人物给以辩证理性的叩问和诗意的解读。换言之,作家寻求一种诗性的历史观和审美化的历史理性,期待一种既有价值判断又必要地悬置判断的哲学智慧融入自我的文本书写。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追求富有美感的结构方式,以象征与隐喻交替的符号表现,自然和典雅相交融的话语修辞,给予阅读者唯美主义的享受,赢得批评家和大众读者的普遍赞誉。
一、历史与文学的本质性差异和同一性关联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历史与文学的本质性差异。然而,不能忽视的另一个事实是,历史与文学存在着同一性的关联,中西都有文史融合的传统。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一方面追求历史题材的间离作用和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和现实时空拉开距离,创造有利于审美观照的心理情境。充分发挥历史题材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和空白点丰富的特性,获得文体的张力,象黑格尔所说的那样,跳开现时的直接性,达到艺术所必要的对材料的概括。另一方面,始终遵循一个美学的前提:敬畏历史和倾听历史。作家不期许今人比古人高明,自我比历史高明,不刻意地修饰历史,不轻易地对历史人物断言“功过是非”。作家首先是谦卑地倾听历史的声音,和历史进行平等的言谈,其次是对历史事物和历史人物持以宁静平和的追问,最后才是对于历史的超越一般意识形态的审美评判和诗意地解答。作家尊重历史的“细节事实”,不越雷池,而这一点恰恰是新历史主义所推崇的理解历史的原则之一。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几个重要集子:《沧桑无语》《面对历史的苍茫》《何处是归程》《春宽梦窄》《千秋叩问》《龙墩上的悖论》《张学良:人格图谱》等都禀赋如此的美学理念。
美学与历史的对话,贯穿着如此的艺术信念:以审美的姿态去理解历史和阐释历史,以诗意的方式去想象历史和书写历史。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不是机械地遵循某种历史观和方法论,也不是单一性地运用某种历史意识去理解历史事件和判断历史人物。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理性只是作家对于历史观察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方式。除此之外,佛学、儒学与道学的历史观以及新历史主义等观点与方法,都是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所借鉴的思想资源。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密切地关联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之谜、历史品评、历史吊诡等内在结构。就历史事件而言,王充闾的书写本着一种实证主义的哲学信仰,表现对于历史细节和事实的客观尊重,秉承着敬畏历史的美学态度。在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阐释方面,则贯穿一种诗意的历史观。以一种“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现象学哲学立场去重新诠释历史和假设历史,给予阅读者审美运思的多种可能性。对于历史人物,作家不是简单地复现“原型属性”,而醉心于勾勒“圆型人物”,力求揭示历史人物的多重心理和矛盾心态,呈现灵魂的多维结构。《青山魂梦》复活两个“李白”:“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两者构成一个整体的‘不朽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用破一生心》揭示理学立命和心许成圣的曾国藩,精神深处交织深刻矛盾和无限痛苦,画出一个处于历史的关节点而聚集着生命复杂性的人物肖像。《他这一辈子》在写出李鸿章的历史悲剧性同时,更描摹出一个性格悲剧和心理悲剧的侧影。《守护灵魂上路》以诗意的感悟,勾画一位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瞿秋白的文学和革命的选择、信仰和命运的冲突,美与爱的分离,这些矛盾冲突被散文诗性化书写之后,重新阐释了一位被历史误解的文人革命家。
人类的理性存在一种追问的本能,对于历史而言,人总是执著于历史之谜的求解。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在对历史事物和历史人物书写过程,当然不放弃对于历史之谜的叩问。然而,与众多的历史文化散文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于,前者喜爱破解历史和证明历史。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采用古典怀疑论者的方式,不是竭力求解历史之谜,而眷注于对历史之谜进行存疑和提问。《陈桥涯海须臾事》以叙事为经,品人为纬,以想象、直觉、体验的意识流方式,将被时间尘封和空间间离的历史画卷以亦幻亦真的意象重现在读者的眼帘。作者以前人何思齐“陈桥涯海须臾事,天淡云闲古今同”的诗句为叙事线索,描绘了三百余年宋王朝的悲喜交加的戏剧,对历史既有理性分析又有诗性随想,融入了通达的幽默与诙谐,以禅家拈花微笑式的生命体悟,借以慧能《坛经》“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的诗性智慧,呈现自我对历史的悲剧式循环的超然理解,辩证的机锋勘破兴衰存亡之物理。历史和人物的万象微尘,逃不脱正觉智慧的佛眼之光。宇宙万有,沧海桑田,都不过属于心识之动摇所产生之影像,内界外界,物质与非物质,无一非唯识所变。作者于是感喟:世界只不过是心灵的幻像式反映,历史像一个玄妙幽秘的无法勘破的谜语,它所能留下的只是存在于精神世界的永恒正义和审美情怀,还有幻觉之中的过眼烟云。散文对历史与人事照之以空幻,观之以虚无,又不乏逻辑公理和道德良知,文本以一种极具想象力的阐释学视界重估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历史的谜团变得不再重要,而主体对于这个谜团的诗意反思却凸显意义。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还眷注于历史的吊诡与历史的悖论。《土囊吟》和《文明的征服》,异曲同工地揭示了历史的背谬:武力征服了文明,最终征服者又被文明所征服。权术攫取了权力,最终又因权术丧失了权力,权力和权术的循环构成血缘政治的历史循环,权力法则最终服从于历史的法则。历史的因果循环体现了佛家的因果报应的理论,生命存在的所谓的“苦、集、灭、道”“四圣谛”均被集聚在宋太宗和金太宗的王朝历史里。历史的悲剧性和合理性被体现在生命终结的黑色阴影里,一个缺乏慈悲心肠的生命个体,必然会得到历史的无情的惩罚,前世的罪孽很可能要得到后世的报应。这也体现了作者的道德逻辑和正义理念。文章既寻求历史之谜的答案,也悬置对于历史之谜的简单设问,渗透的是对善与恶、美与丑,武力与文明、历史与文化的辩证的理性和诗性相交融的思考。
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以审美的方式和历史交谈,以诗意的领悟去心会古人。秉持的历史观念暗合和接近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某些看法。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HaydenWhite,1928—)提出“元历史理论”。他自负于所谓“元历史”(Metahistory)的创见,倾向对历史进行想象性的阐释和理解,历史成为叙述、语言、想象等综合活动的聚合物,被诠释者赋予审美和道德的成分。他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一文中认为:“当我们正确对待历史时,历史就不应该是它所报导的事件的毫无暧昧的符号。相反,历史是象征结构、扩展了的隐喻,它把所报导的事件同我们在我们的文学和文化中已经很熟悉的模式串联起来。”王充闾认为散文创作应该容许适度的想象,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依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意象,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其间必然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作家关切“散文无文”的流弊,主张散文守护文学性和审美性这两个历史相传的要素,既要从政治理性漩涡中,从概念化、意识形态化的僵硬躯壳中挣脱出来,也要超越商业时代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娱乐至上的藩篱,保持作家内在的精神支撑和审美个性。他的历史文化散文写作,贯注着如此的美学理念。散文集《千秋叩问》《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浪之水》《张学良:人格图谱》《龙墩上的悖论》《王充闾散文》等,无不融合历史与美学对话的艺术努力。历史事实与历史细节、历史规律与历史理性在被敬畏、尊重的逻辑前提下,进入到散文书写的层面,历史融合文学创造的想像力和审美领悟,渗透新的语境的价值判断和生命智慧。散文激活了历史,历史在当代语境焕发新的美感。
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闪现出以美学的视角和诗意的领悟,对于历史的探求与追问的艺术色彩。《桐江波上一丝风》显露恢宏的气度和深邃的思理,娴熟地运用空间写时间和时空交错的手法,从地域切入历史与文化,将著名隐士严子陵作为焦点人物,由此牵引出历史上隐士群像,以戏剧主角为中心和群像展览相辅助的方式,深入探索了中国历史上的隐逸现象,揭示了隐逸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内蕴。《春梦留痕》采取虚实相生的梦幻笔法,凭借自我的诗性领悟复现了一个早已消逝但又鲜活存在的文化巨匠——苏轼,揭示他由“临民”、“恩赐”的心态转变为与民一体的心灵轨迹,使原本悲剧性的情致转换为一种超脱宁静的审美意境,写出了一个灵魂的诗化人生。诗人流放儋州的生活,既是戏剧性的,又是诗意盎然的,散文以悲剧氛围开场,却以喜剧化的方式结尾。文本写活了为一般读者所陌生的苏轼,以诗人情怀和审美体悟呈现了一个充满激情和智慧的生命空间,在这个空间,栖居着一个永恒的苏轼。《叩问沧桑》以联想与对比的艺术笔法,将古罗马与洛阳城进行了相似和差异的双重对比,借用北宋大政治家、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的诗句,作为“旧时月色”的隐喻和文笔的线索,以简练的线条勾勒出与洛阳地域有关的历史沧桑,以《麦秀》、《黍离》的古诗和“铜驼荆棘”的预言,寄托着抚今追昔、凭吊兴亡的情感。借用元人诗句“不信铜驼荆棘里,百年前是五侯家”,隐喻历史的沧桑变化。其它诸多篇目,无不寄寓着作家以美学的眼光凝视历史和以诗意的情怀阐释历史的不懈努力。
二、卓荦优异的散文除了富有精妙的哲思和深刻义理之外,还必须呈现一定的文学性和艺术美。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紧扣美学与历史对话的脉络,文本以富于美感的结构方式,象征与隐喻的符号表现,自然和典雅相交融的话语修辞,给予阅读者唯美主义的形式享受。
他的新作《张学良:人格图谱》,由十五篇系列文本结构而成,把“张学良作为现代史上一块人格‘界碑’进行凸显,完成了艰难的精神突围”。黑格尔说:“艺术家的独创性不仅见于他服从风格的规律,而且还要见于他在主体方面得到了灵感,因而不只是听命于个人的特殊的作风,而是能掌握住一种本身有理性的题材,受艺术家主体性的指导,把这题材表现出来,既符合所选艺术种类的本质和概念,又符合艺术理想的普遍概念。”文学创作难题之一,是如何将耳熟能详的题材写出新的境界和新的意象,激发接受者的审美知觉和心理体验,这也是考量作家才情和灵性的一个尺规。《人生几度秋凉》这一文本,一是在写法上以夏威夷的威基基海滩三个串联的画面,勾勒出周身沾染历史尘埃的世纪老人张学良的一生沧桑,借用类似蒙太奇的镜头,以三个美丽而感伤的夏威夷海滩的黄昏为背景作底色。作家笔底生花,轻盈腾挪地勾画出将军闪烁传奇色彩的刚正、悲剧的生命轨迹,点染其忠义倔强、率真仁爱的秉性。文本犹如传统的泼墨写意,笔墨淋漓,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不已。二是文思上独行理路,以一连串命意奇特的假设,提出对于历史和人物的双重疑问,暗藏着多种可能性的历史吊诡和命运玄机。这一节文字,哲理和禅机俱现,颇有些古典怀疑论者的遗风。三是对于人物的心理分析也有一己之见:“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著区别,是率真、粗犷,人情味浓;情可见心,不假雕饰,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整个文章一气呵成,结构上巧妙编织和思理的不落言筌,令人折服。《人生几度秋凉》的结构方式,可谓是类似现象学的“看”的方法:一方面是以视觉的眼睛进行“还原直观”,以三个秋凉的黄昏为审美媒介,纵览少帅的百年人生,体察历史的神秘和偶然。另一方面,是以心灵的慧眼去“本质直观”,领悟生命主体的强力意志、爱的激情、仁的力量、智的空灵和信念的轮回。该文叙事结构的活脱精巧和运思结构的飞扬飘逸形成美妙的双峰对峙。这也许是迄今为止写少帅散文中最为传神和最见美感的篇目。《张学良:人格图谱》出版之后,赢得着评论界多位名家的美誉和广大读者好评,不能不说是近年来散文界不可多见的现象。
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一个重要的审美特性,注重于结构的营造,从构思与立意、叙述与表达的策略、方法、技巧的目的性,无不体现一种智慧性的写作机心,潜藏着作家的艺术独创性和审美形式的提炼。《青天一缕霞》,整个文章从“云”着笔,以象征性的笔法以云的形状、色彩、情态的变幻,以意识流的视角叙述天才女作家萧红才情卓荦、悲凉感伤的短暂人生。“云霞”构成散文结构的眼睛,成为凝视萧红诗意和唯美的生命路程的一串目光。“云”,既是艺术文本的机杼,又是散文意境的纹理,更是创作心理的张力,它成为整个文本的有机结构。伴随着“云”的意象的变幻和递进,文本的思理和情感的足迹也在向深层行走。作者扣住萧红挚友聂绀弩的诗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将文章做得空灵飘逸,才情并茂。“她像白云一样飘逝着,她的世界在天之涯、地之角……云,是萧红作品中的风景线,手稿没有,何不去读窗外的云?”如果说《青天一缕霞》在结构上是以空间写时间,《狮山史影》则以祖孙三代的皇权变更的历史时间,交错着散文结构上的空间变换,揭示出权力对于历史和人性的宰制和操纵。此文堪为绝佳妙文,以时间叙述交织着南北交错的空间,又以空间写行藏,写祖孙相继、叔侄争权的事件。尺牍之文写出明朝几代皇权更替的刀光剑影,以燕王与惠帝的叔侄相煎为主体,连带写涉了整个明史,理性中隐含诗性智慧,运思中潜隐禅意与佛理。该文的结构之目,就是一副楹联,或者说作者的立意和结构方式就围绕这一楹联延展,以它作为串联整个散文的线索和灵魂。一个熟知的历史事件由于精妙的叙事方式和文本结构形式,给予欣赏者的审美感受却是丰富而充满陌生感的。不能不折服于作家的匠心才智。
象征和隐喻是文学性的标志之一,也是阅读者的美感来源之一。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对于这两种方法格外钟情。“象征的特征是在个性中半透明式地反映着特殊种类的特性,或者在特殊种类的特性中反映着一般种类的特性……最后,通过短暂,并在短暂中半透明地反映着永恒。”《祁连雪》一文,以流动的线条摹写了“千山空皓雪”的审美意象,展开对于雪的象征和自由联想。神话与传说作为文本的联想线索,在空间上的不断流动,由此构成了叙事上的时间转移,寄寓丰富的历史内涵。文本灌注着阐释学的理念,力图达到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下的“视野融合”和“效果历史”的解说,凭借新历史主义的意识,获得对以往历史的新的视界的想象和理解并由此进入到对历史的追问。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的众多篇目,擅长运用象征的技法对于历史事件、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的描摹和刻画,呈现鲜活灵动的美感。隐喻这一概念,“在文学理论上,这一术语较为确当的含义应该是:甲事物暗示了乙事物,但甲事物本身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也要求给予充分的注意。”隐喻的笔法在《梦雨潇潇沈氏园》这一文本得以充分显现。“沈园”作为特定的审美空间寄寓着写作对象(陆游)的诗意体验,附丽着延绵的情感时间,凝聚千古词人的爱情守望和绝望的美感,作者以时间空间的渗透和转换,描叙感伤千古的爱情故事。写作主体借助于梦的隐喻,获得充分的想象力和灵感。“梦”作为隐喻的符号,既将“沈园、诗人、爱情、悲剧、诗歌、梦幻”这一系列意象交织一体,又将陆游的诗和梦、爱和死的心路历程予以审美呈现,给接受者以梦幻美的感受。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他提出“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美学主张,将情感·梦幻·艺术视为一体化的精神构成,并在自己的戏剧创作中实践了这一理论。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的不少篇目,借鉴古典美学的艺术理念,表现出梦幻式的隐喻之美。
判定一个作家是否达到美学与艺术的较高境界,标准之一就是看其艺术文本的语言是否具有自我的风格,是否形成自我的独特“话语”。在当今中国的散文界,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以其典雅醇厚与冲淡空灵和谐糅合的语言独树一帜。究其原因,首先,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王充闾的散文语言汲取了古典文学的营养,借鉴古典文学的修辞技巧,诸如双声叠韵、对仗对偶、象征隐喻等。作家禀赋深邃敏锐的汉语语感,擅长于语言的意象格调的建构。创作主体心理结构的深沉睿智,使其文体的语言表述具有醇厚绵密的风味。其次,来源于作家对大自然的审美体验。文本语感的灵敏与鲜活,和王充闾挚爱山水、沉醉自然的生命态度密切关联。对大自然的审美感悟,令散文语言充盈着诗的气质和灵感。尤其近些年的散文创作,冲淡而空灵的语言风格成为其艺术魅力的一部分。最后,作家长期对哲学与美学酷爱,擅长思辨,文本语言也闪烁一定的哲思色彩,充盈着哲理散文的风格。然而,哲理化的语言由于和故事的叙述、景物的描摹结合在一起,没有概念化和抽象化的弊端,令读者易于接受。“语言也不出现于言语者的意识之中,因此语言的意义也远比某种主观行为要丰富得多。”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众多的文本借助语言所隐匿的意义既是丰富的也是充满美感的。
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被关注和评论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件,多年沉醉散文世界的作家终于被众多批评家和读者所认同和喜爱,这是一个有意味的象征,说明文学还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领域,理论批评界和读者都共同关注那些寂寞的审美边缘和孤独的文学世界。王充闾的写作历程证明,创作主体是一个为散文写作而存在的生命个体,美学与历史对话是他数十年书写生涯的不懈渴求。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不以吉光片羽的碎片写作见长,也不依赖矫揉造作的语言夸张和哗众取宠与耸人听闻的过激议论笼络接受者,文本中寄寓着宁静的运思,典雅自然、从容洒脱的话语表达,平等自由的对话方式,期待与古人心会,与今人神往的审美境界,令阅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感受到作者和文本的亲切睿智和澄明通透,感受到童心犹在的纯真和年长者的生命智慧,以及追忆似水年华的感伤和对于历史的诗性的评判,作家的历史文化散文弥散着一种摄取人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