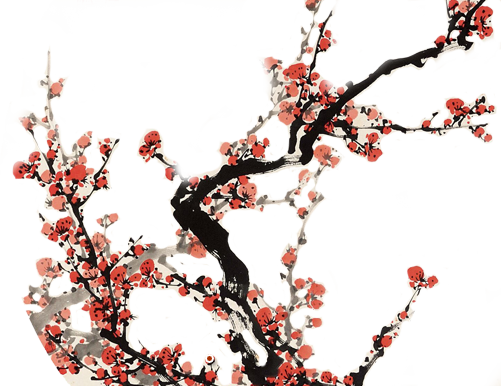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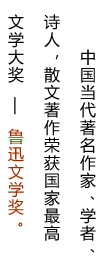

“小大之辩”与“有无之辩”
——《庄子·逍遥游》新析
林榕杰
摘要:在《庄子·逍遥游》中,“小大之辩”揭示了“逍遥游”的主体,因此也可说是“逍遥游”主体之辨。“小大之辩”还涉及与“逍遥游”相关的时空大小之辨。至人、神人、圣人都可说是逍遥游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至人高于神人、神人高于圣人。庄子的“大言”是与“大知”相联系的,人们可借助其“大言”走向“逍遥”与“无为”,因此其“大言”并非无用。惠子认为庄子的“大言”大而无用,与他仅有“小知”而无“大知”有关。在《逍遥游》中,为充分理解“逍遥游”以及“小大之辩”,需结合“有无之辩”。“小大之辩”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局限性大小之辨,而“有无之辩”可说是在特定方面局限性有无之辨。
《庄子》一书共三十三篇,第一篇就是《逍遥游》。此篇揭示了《庄子》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即作为篇名的“逍遥游”。这一篇阐述“逍遥游”主要包含两个视角:一是“小大之辩”,二是“有无之辩”。所谓“有无之辩”,是对“有待”与“无待”、“有用”与“无用”、“有穷”与“无穷”等之间区别的概括。叫以往论者往往重视前一视角,而忽视了与之相关的后一视角。本文在结合这两个视角展开论述时,还会把《庄子》思想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贯穿起来,比如“至人”、“神人”与“圣人”、“言”与“知”等等,这样也有助于读者对“逍遥游”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小大之辩”与“逍遥游"的主体、时空及其他
《逍遥游》篇幅不算太长,但由于作者的意思主要通过并不很易于理解的“寓言”、“重言”、“卮言”等形式表达,加上不同寓言、重言、卮言之间的关系在把握上难度更大,因此历来有种种不同解读。该篇肯定有一主旨,作者通过各寓言、重言、卮言等从不同角度阐述这一主旨,因此我们也应通过各寓言、重言、卮言等从不同角度把握其主旨。另外,将《逍遥游》全篇划分为若干部分并分别弄清各部分的大意也有助于我们逐步把握该篇的主旨。
关于《逍遥游》的层次划分,以往有几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该篇可划分为两部分,比如刘坤生在《(庄子)九章》中提出从鲲鹏变化和大鹏南飞到“三无”境界为一层次,可称为总论;其后的三个寓言是对总论的说明及展开。这种看法与张默生在《庄子新释》一书中表达的观点基本一致。还有人包括释德清认为该篇可划分为三部分:从篇首到“圣人无名”为“寓言”,从“尧让天下于许由”到“窗然丧其天下焉”为第二部分,其后的第三部分为“卮言”。笔者也认为该篇可划分为三部分:从“北冥有鱼”到“此小大之辩也”为第一部分,从“故夫知效一官”到“窗然丧其天下焉”为第二部分,从“惠子谓庄子”到“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为第三部分。下面按顺序来分析这三个部分。
《逍遥游》第一部分末尾点出了“小大之辩”,这是该部分的核心之一。这样,我们分析这一部分时也就应围绕这一核心。而“小大之辩”与“逍遥游”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小大之辩”其实揭示了“逍遥游”的主体,因此也可说是“逍遥游”主体之辨——逍遥游主体是“大者”,而“小者”则不能说是逍遥游主体。
该部分首先讲到鲲化而为鹏之事。鲲、鹏都是大者,“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而鲲化为鹏代表什么意义呢?成玄英的解释是:“故化鱼为鸟,欲明变化之大理也。”鲲化为鹏,表明大者之变化——从无翼变成有大翼且从游于海中转为飞于天上,这样就进入了一个远为广大的空间。
“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从北冥往南冥就方位而言是否有特殊的意义呢?成玄英认为:“所以化鱼为鸟,自北徂南者,鸟是浚虚之物,南即启明之方;鱼乃滞溺之虫,北盖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暗,舍滞求进,故举南北鸟鱼以示为道之迳耳。”成玄英重视“南北之辨”,并将南北与“明暗”联系起来,认为自北往南表示向明背暗。不过对大鹏的“逍遥游”而言,真正重要的是突破空间的局限,而不是由暗向明。
鹏的飞翔是极高的,《逍遥游》中称它“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在这样的高空中飞翔,它又能看到什么呢?“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由这句话可推知鹏的高飞使其进入一个从地面看来是“远而无所至极”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它的视野没有任何的阻碍。地上的生物其视野毕竟受到地面的局限,而高飞的大鹏则突破了这种局限。它不仅近乎“游于无穷”,还由此而“视于无穷”乃至“知于无穷”。
关于鹏的飞翔,《逍遥游》中还提到了风:“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可以这样认为,鹏的飞翔是离不开风的,并需要“积厚”之风。但这是否表示鹏“有待”呢?刘坤生认为“舟大而不能行是受制于水浅,而鹏飞待风的风却是大鹏自己培育而成的”,因此大鹏可说是“无待”。此说不够正确。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大鹏能飞于如此高空,也就不在风中而是在风之上飞翔了——其下则是九万里厚之风——而这种风应是不会止息的。说如此大风是鹏“培育”而成的有些牵强。鹏固然需乘风而飞翔,而其所乘大且能不失其所乘可说是其“无待”的表现。后文接下来提到大鹏“背负青天”,这仍是说它飞之高,而“莫之天阏”的意思是说“什么也伤害不着它,阻挡不着它了”。
这里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鲲、鹏二者是否都为逍遥游的主体呢?就此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一是认为鲲、鹏都不是逍遥游的主体;二是认为鹏是逍遥游的主体而鲲不是,这样大者未必都是逍遥游的主体,而鲲化为鹏可说是大者从非逍遥游主体化为逍遥游主体;三是认为鲲、鹏都是逍遥游的主体,鲲是指逍遥游于海之大者,鹏则是指逍遥游于天之大者。成玄英疏中有:“昔日为鱼,涵泳北海;今时作鸟,腾翥南溟;虽复异沈性殊,逍遥一也。”不过二者当说是不同层次的逍遥游主体——而鹏属于更高层次的主体。对这两种主体来说,其“逍遥游”的空间是不同的,鹏所“逍遥游”的青天远较鲲所“逍遥游”的北冥为大。因此可以说,由鲲化为鹏是主体突破其原来所在的空间进入一个新的更大的乃至无穷的空间。那么,上述三种答案究竟哪种更为可取呢?考虑到本篇的一个主旨是和逍遥游与否相联系的“小大之辩”,而鲲与鹏间一般认为并不存在“小大之辩”,这样二者之间也不应该存在逍遥游与否之别。因此,笔者更倾向于最后一种观点。
庄子未将鲲与其他小而能游者比较,但将鹏与蜩、学鸠、斥鹅等小而能飞者比较——前者飞得高且远,后者飞得低且近。它们飞翔的空间——其实也可看做生存的空间是有重大差异的:小者其飞所至亦小,而大者其飞所至亦大。蜩、学鸠等并非没有意识到其生存空间是较小的,但它们并不想突破这一空间,并认为像鹏那样飞翔于远为广大的空间是无用的。它们对鹏并不理解,反而笑道:“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蜩、学鸠等与鹏的区别不仅是在其飞翔空间(生存空间)上的差异,还在其“知”方面的不同——蜩、学鸠等之“知”为“小知”,不足以知鹏之飞,也不足以知鹏之“知”,且不足以知“逍遥游”。与蜩、学鸠等比较起来,鹏可说是有“大知”的。另外,它可说是“游于无穷”的,而这也是“逍遥游”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庄子》中《逍遥游》这一篇而言,其中的“逍遥游”一方面是指大者(就主体而言)之“逍遥游”,而小者之“游”不能称为“逍遥游”;另一方面是指大处(就空间而言)中之“逍遥游”,小处中之“游”也不能称为“逍遥游”。“逍遥游”包含有消除或突破种种局限之意,因此它也就应与“大者”、“大处”相联系。
关于《逍遥游》中“小大之辩”,除涉及形体大小、空间大小、“小知”与“大知”外,还包括“小年”与“大年”等。庄子提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前面提到的鹏、蜩等可分别视为“大知”、“小知”的象征,这种“大知”、“小知”是与其飞翔空间(生存空间)的大小相联系的。此外,“大知”、“小知”还与特定主体生存时间的长短相联系,换句话说,“知”是受到“年”的限制的。庄子提出“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说明“小知”是受到“小年”限制的。他还举出“大年”的代表,那就是“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这种大椿之“大知”显然会与“朝菌”之“小知”形成鲜明对比。“大知”突破了“小知”所具有的局限,可以说“小知”的局限性大而“大知”的局限性小。而“遣遥游”是针对“大知”来说的,并可说是有“大知”者的“逍遥游”。
《逍遥游》第一部分讲鹏的“逍遥游”除涉及“小大之辩”外,还涉及“有无之辩”。鹏与蜩、学鸠之间有“小大之辩”,人也是有“小大之辩”(包括“小知”、“大知”之辨)以及“有无之辩”(包括“有待”、“无待”之辨)的。这是《逍遥游》一篇随后要讲述的问题。
二、“小大之辩”、“有无之辩”与至人、神人、圣人
在《逍遥游》第二部分,作者围绕“小大之辩”、“有无之辩”引出了至人、神人与圣人。庄子由蜩、斥鹅等物中之“小者”讲到人中之“小者”,指“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这里所谓“知”应是“小知”,所谓“行”、“德”也可做类似理解。此处林希逸的解释是:“此三等人各以其所能为自足,其自视亦如斥端之类。”可以说这几种人的自足、自是,不过是“小知”、“小德”者的自足、自是,因而是不足称的。
至于与他们形成对比的人,庄子首先举出宋荣子。后者“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或可见其“知”已超出世间“小知”。此处成玄英疏为:“荣子率性怀道,警然超俗,假令世皆誉赞,亦不增其劝奖,率土非毁,亦不加其沮丧,审自得也。”宋荣子可说是突破了世间荣辱、毁誉的局限。他除了“辩乎荣辱之境”外,还“定乎内外之分”。不过,宋荣子仍有其不足,于是《逍遥游》中又提到了“御风而行”的列子,“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郭象注为“苟有待焉,则虽御风而行,不能以一时而周也”。列子仍是“有待者”——需要待风而行,且他不能游于无穷,而是在较短时间内就要返回。他的“御风”与大鹏的“培风”应是有重要差别的。而人中还有“无待”者,他们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他们固然有所乘、所御,但与列子的所御还是有区别的。这是因为他们所乘、所御大而能不失其所乘、所御,而这正是“无待”与“有待”的重要区别所在。此处“游无穷”除了有空间上的意义外,或许还有时间上的意义。我们可以说,“无待”者是“逍遥游”的主体,且他们应属于突破空间(乃至时间)的局限者。
在《逍遥游》一篇中,作者进而提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他对三者所作的概括都是否定形式的。三者应分别与“有己者”、“有功者”、“有名者”相对——这些都应该说是有待者。还要指出的是,至人、神人、圣人应是有区别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至人高于神人,神人高于圣人。这在下文中还要详细加以论述。
关于“圣人无名”,尧与许由的对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含义。尧欲将天下让给许由,并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对此许由的回答是:“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尧提到了“日月”与“爝火”等,看来他似乎知道“小大之辩”,然而以他的“知”其实不足以真正了解“小大之辩”(尤其是与“逍遥游”相关的“小大之辩”)。许由似弃天下之大而取“一枝”之小(他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看似不知“小大之辩”,然而以他的“知”其实足以知“小大之辩”,他的“知”可说是“大知”。他以其“大知”而能不求名,从而达到“圣人无名”的境界。
许由与尧之间不仅有“大知”、“小知”之别,还有“逍遥”与“不逍遥”之异。许由并不在乎“名”,也就摆脱“名”的束缚与局限而实现了特定的“无待”,并由此而“逍遥”。他又说“予无所用天下为”,这其实说出了他与尧区别的一个关键之处。可以这样说,对许由而言“逍遥游”是摆脱“天下”束缚的“逍遥游”,而尧则未能摆脱“天下”的束缚。后者并不足以知许由——既不足以知许由的“大知”,又不足以知许由的“逍遥游”。他与许由之间的“小大之辩”,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真伪“圣人”之辨。
在《庄子》一书中,曾在以下两处提到了许由:“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日:‘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日:‘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日:‘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大宗师》)“啮缺遇许由,日:‘子将奚之?’日:‘将逃尧。’日:‘奚谓邪?’日:‘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徐无鬼》)
从这两处可以看到,许由直接表达出对尧的否定,并且认为遵从尧之“仁义”、“是非”是不能实现“逍遥游”的。另外,许由并不认为尧真正实现了天下之治,相反后世会出现“人与人相食”的局面。上述这些有助于我们对《逍遥游》中尧与许由对话的理解。
从《庄子·逍遥游》中讲到的(与尧形成对比的)许由可以看出该篇思想与《老子》思想的一个重大差别——那就是该篇作者不再追求圣人之治在天下的实现。他的“无为”(与“逍遥”相关的“无为”)更多地与“无为之隐”而不是“无为之治”相联系了。
除许由所代表的圣人外,《逍遥游》中还通过接舆与连叔的话谈到了神人。根据肩吾的转述,接舆对神人所作的描述是:“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他的话被肩吾称为“大而无当”、“不近人情”。以肩吾的“小知”是不可能相信接舆的“大言”,他与接舆的差别也是“小知”与“大知”的差别(他与连叔的区别也类似)。他不足以知接舆所说的神人,正如蜩等不足以知鹏一样。
接舆所言神人“不食五谷”或是指其无欲,而他们与俗世的人是有重要差异的。其“乘云气,御飞龙”超过了列子的“御风”,当近似于“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而其“逍遥游”是“游乎四海之外”的,这与“游无穷”当是相通的。与上文提到的大鹏相似,“游于无穷”也应是与“知于无穷”相联系的,因此神人也可说是突破空间(乃至时间)的局限而拥有“大知”的。
连叔对接舆的话进行了补充,他对神人的描述先讲了神人之德——“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这样的神人可以说是“得万物”的,而其“德”则可认为属于“大德”,不同于上文提到的“德合一君”者的“小德”。他们不会“弊弊焉以天下为事”——这就与许由相似。连叔还说神人“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物莫之伤”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或可看作“逍遥游”的前提,并是“逍遥游”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我们可以想到鹏与蜩、学鸠等的另一个区别——那就是鹏的高飞使其不可能受到任何小者的伤害,而蜩、学鸠等并不能实现“物莫之伤”。
连叔还提到“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这样又由神人引出尧舜,并将他们加以比较。林希逸对此的解释是:“谓此人推其绪余,可以做成尧舜事业,岂肯以事物为意!” 张默生的解释与之近似:“言出其所遗之糟粕,犹足以化导尧舜,使其进于无为之治也”。这样看来,神人非不能做成“尧舜事业”,而是其不愿为此。
如果将许由作为“无名”的圣人的代表,他与藐姑射山上的神人应还是有差别的。《逍遥游》中还提到:“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窖然丧其天下焉。”许由不能使尧“窗然丧其天下焉”,这从一侧面反映出他与藐姑射山上神人的差异,而这其实也就是圣人与神人的区别。关于二者的差异,《庄子·外物》中有:“圣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尝过而问焉;贤人所以虢世,圣人未尝过而问焉;君子所以骇国,贤人未尝过而问焉;小人所以合时,君子未尝过而问焉。”从这里可以较明显地看出“神人”是高于“圣人”的。
那么神人与至人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如果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分析起来,二者应是有区别的。不过,《庄子·齐物论》中有:“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该篇中对至人的这种描述与《逍遥游》中对神人的描述是较接近的。
但至人与神人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其最关键的区别点在什么地方呢?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应从“至人无己”来考虑。《庄子·在宥》中有:“大同而无己”,这对我们理解“无己”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可以认为,“至人无己”是指至人因“无己”而摆脱了一己的局限性,并实现了己与非己之一切的“大同”,这样就通过否定“小己”而确定“大己”。
至人、神人、圣人三者尽管有差异,但都可说是“逍遥游”的主体。无论至人、神人还是圣人。应该都是不同程度上的“无待者”。另外,正如鹏与鲲那样,至人、神人、圣人也可看做不同层次的逍遥游主体。而鲲化为鹏,或表明较低层次的逍遥游主体可以转化为较高层次的逍遥游主体。
《逍遥游》在揭示以许由为代表的圣人以及居于藐姑射山的神人后,就转入与“小大之辩”、“有无之辩”相关的另一方面——关于“大言”以及“有用”、“无用”之辩。
三、“小大之辩”、“有无之辩”与“言”、“知”
在《逍遥游》中,连叔称肩吾之“知”有“聋盲”,这种有“聋盲”之“知”也就是“小知”。因此可以说,“小知”、“大知”之辨在某种意义上是知有无“聋盲”之辨,也可看做知有无局限之辨——这是知上的“有无之辩”。这种有“聋盲”的“小知”是不足以知“神人”的,也不足以知关于“神人”的“大言”。只有那些有“大知”者,才能出此“大言”,比如接舆;也只有那些有“大知”者,才能知此“大言”。
至于“大言”,肩吾称之“大而无当”,惠子讥之“大而无用”。《逍遥游》的第三部分是惠子与庄子间的辩论。针对惠子将其言比作“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的大瓠,庄子说了如下的话:“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之“大言”,似无用而实有用。惠子之所以不知庄子“大言”之用,是因为他“犹有蓬之心”,这样他也就没有“逍遥游”之心。关于“蓬”,成玄英疏为“蓬,草名,拳曲不直也”。其实,“蓬”者或还有言其“小”之意(另一方面可能也言其随风飘转而不能逍遥)。
惠子又将庄子的“大言”比作“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的大树,对此庄子则作出如下答复:“子独不见狸狴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藻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狸独与藻牛之间也有“小大之辩”,包括在形体上有小大之不同,另外它们也存在所谓“有用”、“无用”之差别。不过,狸独虽“有用”也有所患(“中于机辟,死于罔罟”),而旋牛看似无用(“不能执鼠”)也无前者之患。如果联系到“言”,可以说“有用”之言也有所穷,而看似“无用”之言也无所穷。
庄子还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他既未否认其言不符合所谓“绳墨”、“规矩”(而这或许正是“大言”的特征),又未否认其言之大,但是他并不因此而认为其言无用,而是提出人们可以借助其“大言”走向“逍遥”与“无为”——而这才是其“大言”真正的用处。显然,这种用处并不是世人所常知的。那么此处“无何有之乡”又是指什么呢?释德清认为它与“广莫之野”都是“喻大道之乡”,此说可为参考。“无何有之乡”更确切些说是指无限广大且没有一切有限物的所在。这样的地方,对以为“大言”无用的惠子而言,是难以将它与“大言”联系起来的。而庄子的“大言”正是要将人们引到这样的所在,并且“大言”只有与这样的“大处”联系起来才能显其用。
这里庄子还明确将“逍遥”与“无为”联系起来。除此之外,《庄子》一书其他地方也有将“逍遥”与“无为”或“无事”联系起来的,比如《大宗师》中有“逍遥乎无为之业”;《天运》中有“逍遥,无为也”;《达生》中有“逍遥乎无事之业”。因此,“逍遥”与否之辨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与“有为”、“无为”之辨相关的。而“无为”则与“无己”、“无功”、“无名”等都有联系。
庄子还提到“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的“大言”也可说是“物无害者”,而后者也是“逍遥”的一个重要方面——能为外物所伤、所害是不能称为“逍遥”的。
至于惠子认为“大言”大而无用,主要因为他“拙于用大”,而这也与他仅有“小知”而无“大知”有关。可以说他不但未真正理解庄子之言,而且未真正明白“逍遥游”。《齐物论》中有:“大知闲闲,小知间间。”按照成玄英的解释,这是指“大知”“宽裕”而“小知”有“分别”。庄子与惠子的言谈也体现了二人之知“闲闲”与“间间”之别。与“大知”对应的是“大言”,与“小知”对应的是“小言”,《齐物论》中又有“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关于“炎炎”,简文的解释是“美盛貌”;关于“詹詹”,李颐的解释是“小辩之貌”——惠子之言正可说是“詹詹”。而肩吾认为接舆之言“不近人情”,又称他本人“惊怖其言”,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对“大言炎炎”的理解。
庄子用“大言”来表达其“大知”,或可说明他并非力求其知其言易为“小知”者所知。对“小知”者以为其言“无用”,他其实并不在意。
《逍遥游》最后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庄子的自我辩护之辞。庄子之言大是因为其所言(如神人等)大,庄子之言看似无用是因为其所言(如神人等)看似无用。另外,庄子的“大言”是与“逍遥游”有关的,而其“大言”是否有用也是与“逍遥游”是否有用相关联的。
在《庄子》一书首篇《逍遥游》中提及“大言”,作者应是在为其全书进行辩护——书中有不少这类大言,会被某些人视为“大而无用”(或“大而无当”)。《老子》一书最后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或是从“信”、“不信”的角度为全书进行辩护,而庄子在此处则是从“有用”、“无用”的角度(并结合逍遥游)对全书进行辩护。
四、结语
“小大之辩”可说是贯穿《逍遥游》全篇始终的一个观念,而它在相当程度上又是逍遥游主体之辨。与蜩、学鸠等不同的大鹏、与“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等不同的圣人、神人、至人还有与惠子不同的庄子都可说是逍遥游的主体,不过他(它)们是在不同意义、不同层次上的逍遥游主体。
为充分理解庄子的“小大之辩”,还应结合《逍遥游》中隐含的“有无之辩”,包括“有待”与“无待”、“有用”与“无用”、“有穷”与“无穷”以及“有己”与“无己”、“有功”与“无功”、“有名”与“无名”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逍遥游”——《庄子》思想中这一核心观念的内涵。有些人仅仅用“无待”来解释“逍遥游”,这可说是不够充分的。最后要说的是,“小大之辩”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局限性大小之辨,而“有无之辩”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在特定方面局限性有无之辨。至于“逍遥”。可说是消除(或突破)种种局限之后所获得的自由。从“逍遥”与“无为”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可以认为实现“逍遥”的过程是消除或突破种种局限的过程,也是不断接近无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