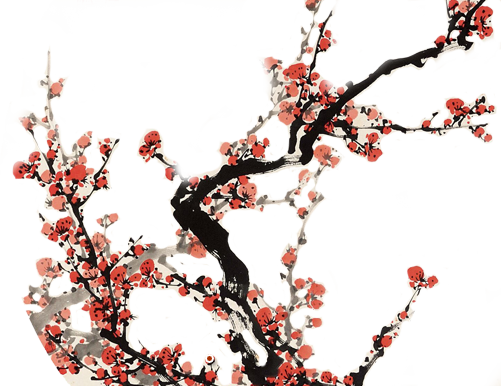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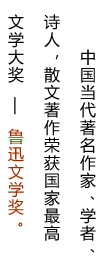

传记写作要写人更要写心
——对话著名作家王充闾
王 研
“传记热”是近年颇受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但热潮背后却隐藏着许多问题。其一,传记类图书种类繁多,出版量极大,但质量却参差不齐;其二,作家对传记主角的描写,背离史实处多,尊重史实处少,出现大量失真、失全之作;其三,缺少有观点、有思考、有厚度的佳作。
对于上述问题,著名作家王充闾也有所关注。4月26日,王充闾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从新书《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说起,对传记写作进行了深入剖析。
如何做到不重复别人,独具特色,别出心裁,这是个大难题……要在万山丛中辟出一条新路,孤峰特峙,迥异流俗
王研:您以“成功的失败者”为题,撰写张学良传记,请问:是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要拟这样一个题目?写这样的人物,空间大,但拘束也多,您觉得写作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最大的满足又是什么?
王充闾:周恩来同志曾经赞誉,“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是一位伟大人物。西安事变挽救了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中华民族促成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时,张学良又荣幸地被列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所以,为这样一位人物立传,我觉得非常值得。加之,我和他是同乡,所谓“桑梓情缘”。我的故里离少帅的出生地只有十几公里,小时候去过很多次,从当地乡亲那里,听到许多关于他的轶闻趣事。乡关故旧,对少帅的人格与德政赞佩有加,每当说起他来,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里面夹杂着几分惋惜、几分悲愤。年轻时我就立下志愿,要把他写出来,再现他的多面、立体形象。
再者,诚如您所说,为他立传“空间大”,就是说他有足够的可言说性——命运起伏跌宕,人性复杂深刻,矛盾冲突激烈,个性空间开阔,可以作多样化解读,其间有着谜一般的代码与能指,可予破译,可供探讨,可加辨析。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他的人生道路曲折、独特,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之所以成为一个言说不尽、历久弥新的热门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充满张力的不可复制的自我,迥异寻常的特殊吸引力。
我的定位是,张学良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出版前,国家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央统战部审定了书稿,认同这一结论。他活了一百零一岁,政治生涯满打满算只有十七八年,却度过了五十四载的铁窗岁月。政治抱负,百不偿一。为此,他自认是一个失败者;同历史上一些悲剧人物一样,张学良也是令人大悲慨、大感伤、大同情的;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多少“政治强人”、“明星大腕”,极其得意,闪电一般照彻天宇,鼓荡起阵阵旋风、滔滔骇浪,可是,不旋踵间便悄然陨落。一朝风烛,瞬息尘埃。而张学良,中华民族将千秋铭记他的英名、他的伟绩。这还不是最大的成功吗?
说到写作上的难度,同我撰写《庄子传》不同——写庄子苦于没有材料,而关于张学良的记述,多如山积,光是传记也得有几十部吧?如何做到不重复别人,独具特色,别出心裁,这是个大难题。当然,在万山丛中能够辟出一条新路,孤峰特峙,迥异流俗,这也是您说的“最大的满足”。
立传属于写史……要靠超拔的史识和科学的史观,在选材、立意、知人、论世方面,做到准确、客观、公正,不溢美,不曲护,恰如其分,实事求是
王研:看得出来,《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这本书,是传记,但又有别于一般的传记,在叙述视角、叙述风格以及叙述方式等多个方面,都给读者带来一种新的体验。同时,二十章既是一个整体,又可单独成篇。从当下的传记创作来看,这样的风格和体例,有一种清新之感。能否请您自己总结一下,这本书与一般的传记相比,有哪几方面的不同?您在创作时,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所得?如果是有意为之,那么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写法?
王充闾:您读得很认真,分析得也很准确。这种写法,是逼出来的,也就是“有意为之”吧。我前面说了,有关张学良的素材,多年来已经挖掘得比较充分。要出新、独创,在材料方面,已无用武之地。您知道,立传属于写史;而写史除了把握史实,还须具备史识与史观。高明的史笔,从不满足于陈述史实,总要做出独到的分析、准确的判断。这就要靠超拔的史识和科学的史观,在选材、立意、知人、论世方面,做到准确、客观、公正,不溢美,不曲护,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写作中,我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于传主的功过是非做出科学的剖析、论证。同时,吸收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和法国年鉴派、美国新史学以及文化心理学、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中的有益养分,透过事件、现象,展开人物心理、个性、悖论、偶然性的解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个性、人格、命运、道路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概言之,就是在坚持事实真实、准确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思维、史家的眼光进行科学的探索,力求达到现代文化立足点应有的高度。此其一。
其二,文体创新。运用多年来创作历史文化散文、描写人物的经验体会,在精心结撰、谋篇布局方面,采取折扇式的叙述方式,以传主的爱国主义的宏伟抱负及其悲剧性的结局为折扇的主轴,然后“并联式”地射出二十支扇股,分别写少帅的人生经历、思想追求、业余爱好,特别是世人最为关注的他的两个人生关节点,或曰“两条辫子”(“九一八”为什么不抵抗,晚年为什么不回大陆);以及传主的三个亲人、四个朋友、两个当事者;最后以《成功的失败者》一章统括全局——古代有个说法,叫做“千里来龙,到此结穴”。这种结构,改变了对于传主从生到死依次道来的传统写法。二十个专题,每个都有不同的视角,互不雷同,却又相互关联,统一于主题中心。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分析:“这本书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传记这种文体的突破上,他将散文的自由表达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有效地结合为一体,提供了一种散文体传记的新的写作方式”;“他将散文体的主观性和鲜明的主体意识带到了传记体中,从而改变了传记叙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传记叙述的思维的逻辑关系是循着传主的生命轨迹而构建的话,那么,王充闾在这部传记中所表现出的逻辑关系则是在自己解读和体悟传主生平的思想脉络上构建起来的。”
其三,传记是历史,我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写,就是说不以单纯的叙事为满足,还通过文学的手法,运用文学的语言,借助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穷原究委,探赜烛微。既保证了叙事写实的客观性,又体现了鲜明的文学色彩和主体意识。
最近,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推荐二十部好书,本书有幸入列,它的推荐理由是:“本书以独特视角客观再现张学良传奇一生,叙述角度新颖,完全不同于常规的传记著述。作者以史实为依据,选取传主与他人的关系进行叙说,并间以传主的自述,夹叙夹议,全书带有人物评传的味道,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纪实文学作品。”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传记应该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
王研:当下,传记在市场上很热,但大多数是为出版而出版。能不能谈一谈您对传记创作的一些想法,您怎么看待当下传记创作的现状?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同时又兼具历史书写的功能,您认为传记应该怎么写?
王充闾:传记属于历史范畴。唐代刘知几有言:“史书者,记事之言也。”说明我国史书传统是以记事为主(司马迁的《史记》属于特例)。而西方传记则注重人的思想、人的精神风貌、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应该说,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无一不与人物紧密联结着。历史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应该成为史家关注的焦点。广大读者期待着通过阅读传记来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历史、叩问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乐。“文学是人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传记应该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
王研:许多作家写传记,更多地把笔墨放在人物跌宕起伏的经历上,特别是情感经历,通过增强故事性来吸引读者。我注意到,《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这本书更关注张学良的性格特质与心态转折,以充满哲思的笔触来重新审视张学良的人生经历。您是否认为,把作者的思考与传记主角的故事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呈现,互为推进,能够写出更有深度的传记?
王充闾:我的立足点是给少帅“写心”,模塑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形象,亦即着眼于展现传主及有关人物的个性特征、内在质素与精神风貌。这就要运用文学语言,调动心理描写、形象刻画和广泛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段。我是这样为定居于夏威夷的晚年张学良画像的:“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唐·吉诃德,后来化身为头戴紧箍、身压五行山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流寓孤岛的鲁滨逊。”
张学良的性格特征是极其鲜明的,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一是活泼、好动,反应灵敏,喜欢与人交往,情绪易于冲动;二是正直、善良,果敢、豁达,率真、粗犷,重然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三是胸无城府,“玻璃人”般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而另一面,则不免粗狂、孟浪、轻信、天真,思维简单,而且,我行我素,不计后果。
这种性格和气质,有一定的先天因素,而更多的是受一定思想、意识、信仰、世界观等后天因素的影响,它们制约着张学良的行为,影响着他的命运——休咎、穷通、祸福、成败。揭示张学良的个性的形成,是读者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从他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社会交往、人生阅历四个方面加以剖析。四个方面形成一种合力,交融互汇,激荡冲突,揉搓塑抹,最后造就了张学良的多姿多彩、光怪陆离的杂色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