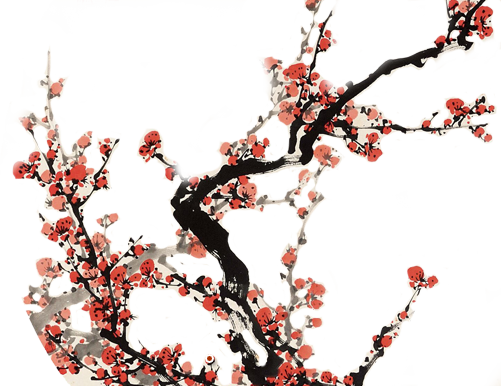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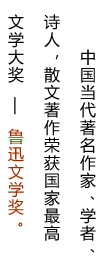

文章与我
——在“人教杯”语文教学研讨大会上的演讲
(2023年8月16日)
王充闾
编者按:王充闾先生以语文教材作者代表身份,应邀出席在大连-召开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第十三届“人教杯”语文课堂教学研讨会议。会议安排三位学者在大会上演讲:另两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全国中学语文教材编委会主任温儒敏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立军教授。
承蒙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厚爱与推重,应邀参加这次盛会,并安排大会上发言,我深感荣幸,当然也心怀忐忑——唯恐谈不出新意,空耗各位的宝贵时间。实际上,我这是第二次参加人教社的大会了,2012年在江西星子县曾出席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作者座谈会。
说到教村课本,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庄严而神圣的。当年考入中学后,尽管讲不出更多道理,只是出于尊师重道,总是虔诚地听讲,悉心地记诵。待到大学毕业,我也登上中学语文讲台,知道了手中的教材课本,都是经过语文专家和一线优秀教师们精心选择,进行过大量基础性研究,并经过多层次的实践检验,因而符合语文学习规律、体现语文素养的知识点、能力点,那种敬谨心情就更加强化,即便后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成为散文作家,也未曾消减。
大约始于1992年,拙作《换个角度看问题》,先后进入人教版的九年义务教育四年制初中语文课本和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课本,期间,陆续收到京、津、沪、粤、苏、鲁等地出版单位寄来的其他文章入选大学、中学语文课本样书。我深知,语文学习关系到亿万青少年的成长,不仅担负着思维能力、审美情操的培养和文化传承的使命,而且有助于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民的素质。应该说,作品能够入选语文教材,确是一个作家的殊荣;当然,同时我也感受到所肩负的社会责任。鲁迅先生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正是本着文学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唤醒、提升、引领作用,因而他满怀深情地说:“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辈作为提供正能量的参与者,即便只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也加倍感到责任的重大。
下面就几篇入选人教版的中学课本的散文作简要说明,或可有助于语文老师教学中剖析、研判。
关于《两个李白》。李白是我素所景仰和喜爱的伟大诗人。他的许多诗文我都能背诵,我曾专程访问过他晚年流寓的皖南,有时竟沉酣在一种幻觉里:山程水驿,雨夜霜晨,每时每地,都仿佛感到诗仙就在我的身旁,我深为他的穷途失意、所如不偶,感到不平和憾恨。但也觉得,他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穷愁、狂放、醉梦、孤独,导致“蚌病成珠”,登上诗国的巅峰。我酝酿着就此写一篇散文。其时是1995年,我担任省委宣传部长。正值省作家协会换届。前任主席是一位小说家,上任伊始,雄心勃勃,高自期许,想要干一番事业,可是,由于缺乏应有的素质与经验,不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结果和党组书记、和老作家矛盾激化,陷身漩涡之中不能自拔,弄得焦头烂额,创作也无从谈起。省委决定由我兼任作协主席。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联系到意念中的李白,确定调整思路,深化主题。最后写成各位看到的《两个李白》。
就文体论,这是带有论说特点的文化散文。现今的论文,逸出散文之外;可是,《古文观止》中的论说文,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钱钟书先生的《谈中国诗》,文质兼美,重思想,有文采,都是标准的散文。这类文章读多了,记熟了,自然会受其影响。苏东坡的《贾谊论》劈头就说:“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我写《两个李白》开篇也说:“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两者构成了整体的‘不朽的存在’。”都是一语破的,统领全篇。此其一;
其二,就内容说,重点分析“两个李白”现象产生的主客观因素——文化基因、个性特征、盛唐之世、封建体制等。
其三,解读李白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心路历程及其穷通际遇所带来的苦乐悲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以至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其四,再扩展一层,揭示人类生存的庄严性、深刻的悲剧精神,以及人性弱点、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火把节之歌》为记事写景散文。1998年7月,由中国作协组织,我到凉山彝族自治区采风。彝族人民能歌善舞,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西汉时期,司马相如就在《子虚赋》中记载了彝族先民的“颠歌”。这里的男女老少皆擅弦歌,转喉开口,一唱百和,视弦歌为自然流露心声的情感通道。他们自豪地说,彝家的史书记在弦歌之中。再就是热情好客。主人早早地欢聚村头,为作家们置酒接风。一队靓装丽服、美目流盼的彝族姑娘,手里擎着酒杯,高歌侑酒。我以素无饮酒习惯为辞,姑娘们便齐声唱着:“大表哥,你要喝。你能喝也得喝, 不能喝也得喝,谁让你是我的大表哥!喝呀,喝!”在这种情真意切的态势下,别说是浓香四溢的美酒,即使是苦药酸汤,也不能不倾杯而尽。最重要的民俗是爱火、敬火。他们把火看成是能够净化一切的圣物,火是中心,哪里有了火,那里便会围上一圈人,火成了凝聚人们的轴心。 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日——火把节,实际上,是彝家古老的祭火节。人类最初一代的文明,是被火的光焰照亮的。
《换个角度看问题》写得比较早。1986年,我任营口市委副书记,分管教科文卫工作。改革开放正处在云程发轫的初始阶段。在全市科普大会上我有个讲话,题为《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 破除思维定势》。为了准备这个讲稿,我开了几个座谈会,向科研人员请教,搜集了大量现实中的实际问题、生动事例。大约有七千多字。当时,恰值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随笔》专栏约稿,我就把这个讲稿加以提炼,整理成1800多字,发表了。由于字数限制,压缩掉许多事例,比如著名科普学家阿西莫夫的故事:这天,一个汽车修理工对他说:“嗨,博士,我来考考你的智力。”阿西莫夫点头同意。修理工说:“有个聋哑人,想买几根钉子,就来到五金商店,向售货员比画了一个手势:左手食指立在柜台上,右手握拳做敲击状。售货员便给他拿来一把锤子。聋哑人摇摇头,售货员就明白了,他是想买钉子。聋哑人满意地走出商店。接着进来一个盲人,想买一把剪刀,请问,盲人将会怎样做?”阿西莫夫顺口答道:“盲人肯定会这样——”他伸出食指和中指,比画出剪刀的形状。汽车修理工笑着说:“盲人开口说就行了,干嘛要做手势?”阿西莫夫红着脸说:思维定势太可怕了。
说过了“文章”,下面讲“我”。
我曾接受过香港大公报、中华读书报记者的几次采访,向我提出大量问题,其中与本次会上我要讲的相关的有:(1)你的“童子功”是怎么养成的?(2)在学术视野、知识结构方面,你是如何实现现代文史哲美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接、融合的?(3)从政多年,担负重要领导职务,同时进行业余创作与学术研究,你是如何解决“双栖之累”,保持创新活力的?(4)退出领导岗位之后,继续挑战自我,完成重要作品多部,这股后劲哪里来?
几个问题基本上概括了“我之为我”,也就是我的成长历程。限于时间,这里只能概括地说一下。辽海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譬如登山——我的成长之路》,那里有详尽的忆述。
一、童子功。
我的故乡是一个紧邻芦苇荡的荒村。当时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日本“皇军”和伪保安队,在这一带不敢露面,结果这里便成了一处“化外 ”之地。我有个族叔,家庭富裕,本身也有学问,有个独生子,顽皮、好动,成天招惹是非。叔叔便聘请有“关东才子”之誉的刘璧亭先生前来施教,我有幸跟着借光读书。因为叔叔也实际参与,实际是两位塾师管教两个玩童,青灯黄卷,八载寒窗。塾师教学有几个特点:
一是,强调背诵,增强记忆力。他们说,“幼童背书,和入室窃贼偷东西类似,先把偷到的财物一股脑儿抱回家去,待到消停下来,再打开包袱,一样样地细看。”这是因为,十二三岁之前,人的记忆能力特强,尔后,随着理解能力的增强,记忆能力便减退了。因而必须抓住这个黄金阶段,把需要终生牢记的内容记下来。有人问了: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根本不懂得书中道理,背下来有啥用?老师的答复是:传道、解惑和知识技能的传授,有所不同。比如,学数学,要一步步地来,不能跨越,初等的没学习,中等、高等的就接受不了。而传统儒学讲的人情道理,经史诗文中的奇思妙蕴,许多情况下,是依靠感悟、细加涵咏的,纵使当时不明白,可以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逐步地加深理解。宋代文学家苏辙有两句诗:“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私塾具体做法是,因为古书没有标点,老师先用蘸着朱砂的毛笔,给我们的书断句。然后,每天分章分段,诵读和讲解。当天的课业讲完了,就要我们大声诵读,晚上还有自习,以三排香为记(大约两个小时);第二天上课,首先就是背书。然后又开始讲授新的章节。下一天背诵时,还要带上前两三天的书,以巩固记忆;主要是按顺序背,有时也选出以前背过的提问。(比如,已经背诵《诗经·小雅》了,又提问《秦风·蒹葭》。)由于有童子功,我的记忆力至今还是比较强的。看到一首陌生的七律,琢磨两遍,就可背诵。
二是,启蒙阶段,注重小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认为这是基础的基础。《三字经》讲“详训诂,明句读”,教课过程中,特别关注读音、断句。这为诵读、背诵创造了条件。刚才北师大王立军教授讲座中,集中谈了文字学,我这里不再重复。
三是,八年中的后三四年,实行读写结合,培养学生写作能力。为此,在“四书五经”、老庄荀韩之外,加上《史记(列传部分)》《古文观止》《古唐诗合解》,强调反复诵读。老先生不同意晚清王筠“儿童不宜很早作文”的观点,认为“只读不作,终身郁塞”,儿童如果一味地强读硬背,而不注意训练表达、思考的能力,就会把思路堵塞得死死的。小孩子也是有思路的,应该及时引导他们,通过作文,进行表达情意、思索问题的训练。许多饱学的秀才写不出好文章,和食古不化有直接关系。当时,从《对句》入手,练习作诗和拟对联;学写纪游、论说短文,并认真指导、修改。
记得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说:“中国人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做一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
二、挑战自我,补齐短板。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文坛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小说界呈现出“寻根文学”与“现代派”双峰对峙的局面。美学界就“美的本体”等基本问题,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争辩,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一时间,西方的哲学、美学、历史、文学等各种著作被大量译介过来。这对于封闭已久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敞开一个全新的视野。如果说,这对于我,是催生变革的外因的话;那么,我自身的认识与需求,便形成了内在的动力。清夜无眠,幡然自省,觉得自己面临着一系列急待解决的课题:知识结构不够完整,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腿比较粗,而现代人文学科缺乏坚实的基础,缺乏现代思维方式、科学精神、理论架构的支撑。还有一点:供职于省市领导机关,在分析问题、处理复杂事务方面积累了经验,认识问题比较客观、全面; 但是,在洞明世事的同时,从一定程度看,规范性、程序化的工作流程与思维方式,影响、制约了探索意识与创新能力。对一个渴望超越的作家来说,这是必须突破的关隘。于是,我在文大期间精读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基础上,又花费几年时间,深入研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的《美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丹纳的《艺术哲学》、卡西尔的《人论》等哲学、美学名著;同时,也研读了法国年鉴派史学、美国新历史主义著作。期间,还有计划地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这样,一直延续到到整个90年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文史哲美的学习、研索,迄未间断。
200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组织“中国作家北大行”活动,先后请十位作家,我是第一个登场的,讲《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期待与深度追求》。在与几位知名教授交谈中,他们提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现在上下都十分重视;但是,专家队伍处于青黄不接状态,年轻的功底不足,七八十岁以上的精力受到限制。你有国学功底,又是作家、学者‘双肩挑’,应该发挥这一优势,集中精力在传承国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多下功夫。”这对我是个有益的提醒。特别是习总书记諄諄告诫:“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丢了这个‘根’和‘魂’”。这更使我明确方向、增强了动力。十年间写出《国粹》《文脉》《庄子传》《诗外文章》等多部作品,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的解读经典,与一般的有所不同。其一,温故重在知新。同样是精读原著,但由于童年时下过苦功背诵,于今许多语句仍然烂熟于心,现在旧籍重温,主要是探求新知。如晤故人,前尘旧事无须再问,今日重逢,最想知道的是别后新的发展变化。其二,着眼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创作、讲学的需要,而非系统、全面的学术研究,多少带点“六经注我”的味道。其三,知识、学问之外,充分重视人生感悟,体现主体意识,联系自身实际。
三、保持创新活力,做到与时俱进。
对于一个作家,创造性思维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步入老年,世事惯经,沧桑历尽,头脑容易固化,形成思维定势,解决这个问题,尤为至要。
这里有个认识问题。长时期以来,人们将读书学习的基点定在掌握知识上,其实,更值得重视的是人生智慧、哲学感悟。知识存在三个层次:一是搜罗信息,二是积累学问,三是增长智慧。大部份知识都是专门的,各种具体知识之间很难会通,但当它升华为理念、感悟、智慧,就可以豁然贯通。我国记录哈雷彗星,始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613年,两千余年从未间断,总共出现过31次。这可以称作“世界的唯一”。但是,记是记了,却没有人对它进行思索、研究,不知道这出现了31次的是同一个星体。到了1875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没有掌握这份天文记录的情况下,只是依照牛顿的引力定律,计算出了彗星的轨道,预言了它出现的周期——每隔76年就会回归到太阳身边一次。可见,信息、知识固属重要,而从知识再出发,进而发现规律,成为智慧,那要重要多少倍。
我学哲学,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抓住两个关键环节,一是注重视角选择。应该说,哲学研索本身就是视角的选择,视角变换,阐释出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这是庄子讲的。考察一个人是否具有哲学思维,首先要看他有没有哲学视角。选准视角,关乎哲学在客观实际中的具体体现与应用。二是调整思维方式,善于提出问题。思想大于存在。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实际上,更应倡导作家成为思想者,因为学者未必就是思想者。有些作家很聪明,文章也流光溢彩,可就是缺乏思想含量,内涵空虚,读过之后,获益无多。同样,作为读者,也应该善于思索,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我读历史,也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从前的史学往往注重史实与过程的记述,着眼于历史的客体;而自从分析的历史哲学提出以来,历史哲学家的重点,就逐步转到了主体如何认识历史的客体上来。我国古代史学以叙述为主,阐释为辅;而现代史学,则以阐释为主,叙述为辅,在记述史实、事件基础之上,着眼于史论,重视历史研究。这里一个前提,是读史、写史要坚持唯物史观。
为了激发思维活力,我喜欢读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作品,像博尔赫斯、福尔摩斯、卡尔维诺的小说,易卜生的戏剧等。我在南开大学讲学,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拉美作家群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创作散文也是,我喜欢“啃硬骨头”,写那些性格鲜明、个性突出,阅历丰富、思想复杂、命运曲折,处境矛盾、灵海熬煎、形象多面,亦即所谓“言说不尽的历史人物”,像列夫·托尔斯泰、歌德、李白、瞿秋白、张学良、曾国藩等。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都可以充分展现创造性思维的张力。
四、充分利用业余时间。
人才成长规律表明,如何利用业余时间,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爱因斯坦甚至说:“人的差异主要在于业余时间。”鲁迅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天才,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把别人聊天的时间、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了工作和学习上。莎士比亚在成为戏剧大师之前,是一个勤杂工,剧本创作属于他的业余爱好。智利诗人聂鲁达,作为正式的外交官,他那些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诗篇,同样也都是业余时间的产品。业余时间既能造就杰出人才,也完全可能生产出庸人、懒汉、酒鬼、赌徒,不仅工作业绩有别,更区分开人生道路的歧异 。
我的文学之路,一直是在繁重的政务夹缝中展开的,所谓“文政双栖”。这样,自是加倍的劳碌。无论节假日、早午晚,除了“三餐一梦”,一切工余之暇,我都攫取过来用于读书、写作。出行乘车,我都要带上书:一般是利于思考的、需要背诵的。即使每天凌晨几十分钟的散步,也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甚至睡前洗脚,双脚插在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卷浏览,友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业余状态下的创作、研究,除了时间冲突,还有一个心态问题,也就是需要有个心灵的自在空间,需要沉潜到文化与生命的深处。我喜欢思索,脑子从不休闲,不懂得“百无聊赖”是什么滋味,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这样一来,生活是否过于清苦、单调,缺乏应有的乐趣呢?每当听到朋友们的这类询问,我总是会心一笑,戏用庄子的语式以问作答:“子非我,安知我不以此为乐耶?”情有所寄,就能顺心适意。读书、创作、治学,本身就是一种寄托,实际上也是一种转化,化尘劳俗务为创造性劳动,化空虚为充实,化烦恼为菩提。上个月,新民晚报刊发我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乐在忙中》。那里引证百岁老人、漫画大家方成先生一首打油诗。诗题在自画像上:方老骑着一辆自行车,前边车筐里满载着笔墨纸砚,后座上驮着高高的一摞书,诗句是:“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