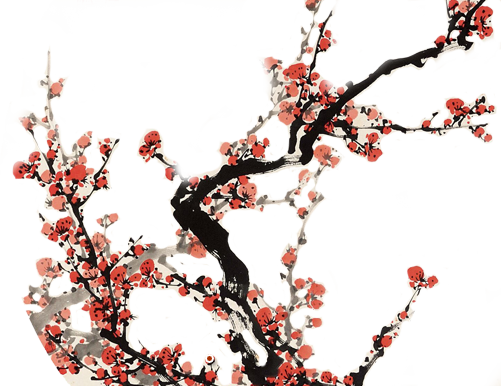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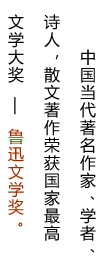

海丹青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著名对话,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迷雾,在王充闾先生的《寂寞濠梁》中获得了崭新的生命。这段看似简单的对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与“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在中国思想史上激起的涟漪从未停息。王充闾先生以他特有的历史敏感与文学想象,将这一哲学对话重新置于现代语境中审视,揭示出其中蕴含的永恒命题:人类认知的边界、主体间性的可能,以及在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如何守护心灵的诗意。本文将从三个维度展开对《寂寞濠梁》的深度解读:首先剖析文本如何重构庄惠对话的哲学内涵;其次探讨王充闾先生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回应现代性困境;最后阐释这一古典对话在当代语境中的再生意义。
《寂寞濠梁》首先是一部关于认知可能性的深刻冥想。王充闾先生以他特有的细腻笔触,还原了这场著名辩论背后被忽视的情感温度与生命体验。在传统解读中,庄惠之辩常被简化为相对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对立,庄子代表审美直觉,惠子象征理性分析。然而王充闾先生穿透这一二元对立,揭示了两种认知方式的内在统一性:“当庄子说‘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时,他并非在陈述一个生物学事实,而是在进行一场诗性判断;当惠子追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时,他并非否定认知可能,而是在捍卫思维的严谨。”王充闾先生敏锐地捕捉到,这场辩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它展示了人类认知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诗性的共情与理性的质疑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寂寞濠梁》中,王充闾先生将这场古典对话置于存在主义的光照下重新诠释。他写道:“濠梁之上的两位思想家,一个在体验‘物化’的狂喜,一个在承受‘异化’的焦虑。”这一解读赋予了古老文本以现代哲学深度。庄子“知鱼之乐”的断言,在王充闾先生笔下成为对海德格尔“在世存在”概念的先声——一种主体与世界的原初统一尚未破裂的存在状态。而惠子的质疑则预示了现代认识论的主体-客体分裂困境。王充闾先生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表明,庄子的“知”不是科学认知,而是一种“参与式理解”,是通过打破主体与客体界限而达到的更高真实。这种解读既忠实于庄子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又赋予其应对现代性困境的启示意义。
王充闾先生对濠梁之辩的文学重构,特别强调了“情境”的重要性。他指出,这场对话发生在“濠梁之上”,而非庙堂或书斋,这一空间选择绝非偶然:“水是流动的隐喻,桥是连接的象征,鱼则是自由精神的化身。”在《寂寞濠梁》中,王充闾先生以诗意的语言描绘了这一场景的氛围:“暮春时节的暖风,微微波动的水面,倏忽往来的游鱼,以及两位思想家长袍飘飘的身影。”这种情境还原不仅具有文学感染力,更暗含深刻哲学意蕴——真正的智慧产生于生活世界,而非抽象思辨。王充闾先生借此暗示,现代学术的专业化、体制化已经使我们失去了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哲学思考的能力与习惯。
《寂寞濠梁》的深刻之处在于,王充闾先生并未停留在对古典文本的诠释上,而是将其转化为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犀利剖析。在工具理性全面主导的当代社会,“寂寞”不再只是濠梁之上两位思想者的心境,更是每个现代人的基本生存体验。王充闾先生写道:“现代人站在自己建造的立交桥上,脚下车流如织,却比庄子惠子更加寂寞;我们有千万种联络方式,却失去了对话的能力。”这种寂寞源于意义的丧失——当一切都被量化、工具化后,生命本身的诗意维度被无情消解。王充闾先生通过对比古今,尖锐地指出:“古人尚能争论鱼之乐,今人却已忘记问自己是否快乐。”这种遗忘是现代社会最深刻的异化表现。
面对这种现代性困境,王充闾先生在《寂寞濠梁》中暗示了回归庄子智慧的路径。他特别强调了庄子“无用之用”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批判价值:“在一个一切都被要求‘有用’的时代,守护某些‘无用’的价值恰恰是最为急迫的精神需求。”濠梁之辩中对“鱼之乐”的关注,本质上是对非功利性价值的肯定。王充闾先生以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这种价值:“就像春日里无人注意的野花,它的开放不为什么,它的美丽不需要观众,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效率至上的世界的一种温和抵抗。”这种抵抗不是激烈的对抗,而是通过守护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自主性,来维持不被完全工具化的精神领地。
《寂寞濠梁》最动人的部分,是王充闾先生对“对话”本质的思考。他指出,庄惠之辩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依然鲜活,正因为它是“真正对话”的典范:“两位思想家虽然立场相左,却共享对真理的真诚追求;他们相互质疑,却从未互相贬低;他们思想碰撞,却保持着人格的相互尊重。”在王充闾先生看来,这种对话精神正是当代社会最为匮乏的:“我们有的是辩论,却少有对话;有的是争吵,却少有交流;有的是信息交换,却少有心灵沟通。”《寂寞濠梁》通过重温古典对话,暗含了对当代公共讨论品质的深切忧虑与隐性批判。
王充闾先生的文学表达在《寂寞濠梁》中达到了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高度统一。他的语言既有学者的精确,又有诗人的敏感。在分析庄惠之辩时,他能精确辨析“安知”二字在不同语境中的微妙差异;在描写濠梁场景时,他的文字又充满画面感与音乐性:“暮色渐渐笼罩濠水,两位辩论者的身影拉长,融入渐渐升起的雾霭之中,只有他们的声音还在水面上轻轻回荡。”这种表达既营造出深远的意境,又象征着思想超越时空的永恒回响。王充闾先生的文体融合了散文的流畅、论文的严谨与诗歌的凝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抒情”风格,这使《寂寞濠梁》既可作为哲学文本来解读,又能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看,《寂寞濠梁》代表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努力。王充闾先生既没有盲目崇拜古典,也没有简单以西学解构传统,而是让古典智慧与现代问题展开平等对话。他对庄惠之辩的诠释,既避免了将其现代化为存在主义或现象学,又使其能够回应现代人的精神困惑。这种方法论启示我们: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不在于提供现成答案,而在于激发新的思考。正如王充闾先生所言:“濠梁上的问题没有终结答案,但它永远警醒我们思考认知的边界与可能。”
《寂寞濠梁》最终指向的是一种“诗意栖居”的可能。在技术统治日益加强的今天,王充闾先生通过对古典文本的重新发现,暗示了抵抗全面工具化的路径——恢复对世界的审美关系。庄子“知鱼之乐"”本质上是一种审美判断,它不依赖科学验证,而源于心灵对万物的共情能力。王充闾先生写道:“当庄子说鱼乐时,他是在进行一场诗性行为,将人的情感投射入自然,又在这种投射中体验更大的自由。”这种诗性认知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现实更深层的参与。在《寂寞濠梁》的结尾,王充闾先生以令人回味的方式总结道:“也许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知道鱼是否快乐,而在于保持询问鱼是否快乐的能力与兴趣。”
王充闾先生的《寂寞濠梁》以其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表达,为我们这个技术狂热而精神贫乏的时代提供了一剂清醒剂。通过重温庄惠之辩,他让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越来越强调“有用”的世界里,如何守护那些“无用”却使人生值得过的价值;在一个越来越依赖技术媒介的時代,如何恢复直接体验世界的能力;在一个意见纷争却缺乏真正交流的社会里,如何重建理性而富有温情的对话精神。濠梁之上的寂寞,本质上是思想者在工具理性霸权下的孤独;但正如王充闾先生所暗示的,这种寂寞中也可能孕育新的希望——当我们重新学会询问“鱼之乐”时,我们也许正在找回被现代性遮蔽的那部分人性。
在《寂寞濠梁》的字里行间,王充闾先生完成了一项艰难而珍贵的工作:让古老的智慧在现代语境中重新开口说话,并让我们听见其中与自己时代息息相关的声音。这不仅是学术的传承,更是文化的再生;不仅是文学的创作,更是精神的救赎。当我们在王充闾先生的引导下再次驻足濠梁,凝视水中游鱼时,我们或许能够短暂地挣脱现代性的铁笼,体验那种“无待”的自由——这才是《寂寞濠梁》留给读者最宝贵的礼物。
【作者简介】海丹青,女,1984年生,辽宁营口人。现任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辽宁省委党刊《共产党员》特约记者、营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传记学会会员、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理事、研究员、“营口之窗”特约撰稿人,营口大型文艺文化演出活动特约撰稿人。曲艺相声作品《趣说东北》、《名歌杂谈》登上中央3频道;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一川烟雨》荣获中宣部、中国文联“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国家奖。多篇散文作品发表于《海燕》、《辽河》、《特别关注》(湖北省委)、辽宁省委党刊《共产党员》、《党史纵横》等刊物;多篇理论文章刊载于《采写编》(河北省委)、《新闻研究导刊》(四川省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