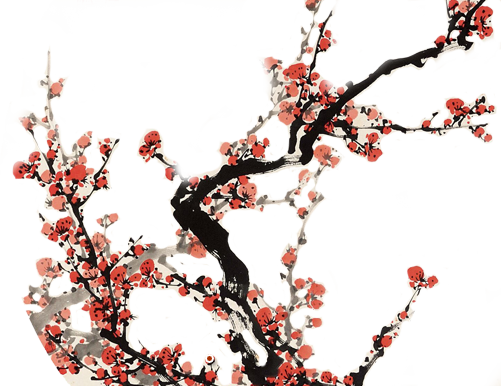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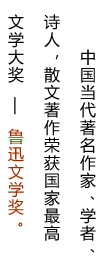

诗之内外
孙 郁
想起来我自己读古诗的经历,附庸风雅的时候居多,真的沉潜下来的时候寥寥无几。许多词句似乎记得,但却不能言之一二,好像朦胧得很。常常的情况是这样,遇到诗人作品的时候,目光在动人的句子间流盼,只是一时惊异,很快将视线滑落到别地了。
这是不求甚解的阅读,自然不能得到真趣。有一年听过叶嘉莹先生的关于古诗词的演讲,颇为感动。后来与友人去她家里拜访的时候,见其对于古诗词的痴迷,以及诗句内化于心的样子,才知道,古代文人的遗绪对于一个人是多么重要。至少是叶先生,生命的一部分就在那些清词丽句里。
这样的人可以找到许多。我的前辈朋友中,王充闾算是一位。他自己写旧体诗,也研究诗文,对于古人的笔墨之趣多有心解。晚年所作《诗外文章》三卷本,乃诗海里觅珍之作,读后可知见识之广,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因诗而望道的人。
王充闾早年有私塾训练,对于古代诗文别有感觉。他是学者类型的作家,对于古代文学的认知不都在感性的层面,还有直逼精神内觉的理性领悟。阅读作品时,涵泳中灵思种种,流出诸多趣谈。但又非士大夫那样的载道之论,而是从现代性中照应古人之思,遂多了鲜活的判断。我阅读他的书籍,觉得不是唯美主义的吟哦,在对万物的洞悉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学问的积累,还有生活经验的对照。心物内外,虚实之间,不再是隔膜的存在,作者看到了人世间的阴晴冷暖。从诗歌体悟人生哲学历史,这个特别的角度也丰富了他的散文写作。
进入诗歌王国会有不同的入口,每个人的经验不同,自然看到的隐喻有别。王充闾在浩瀚的诗歌里不仅感到古人感知世界的方式,重要的是窥见了内中的玄机。我发现他掌握的材料颇多,又能逃出俗见冷思旧迹。中国古人不是以逻辑思维观照万象,而是在顿悟里见阴阳交替,察曲直之变。《诗外文章》里就捕捉到古代诗作里的思想资源,且悠然有会心之叹。古人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方式今人不易理解,但细心究之,在体味中,当可演绎出丰富的观感。
我很感慨王充闾在旧诗里的诸多发现。作者提炼了许多有趣的内质,比如“美色的悖论”“知与行的背反”“大味必淡”“清音独远”“智者以盈满为戒”“论史者戒”等,都是词语背后的意绪。其中庄禅之意依稀可辨,文史哲间的精要点点,牵出幽思缕缕,在似有似无之间,聆听远去的足音带来的妙悟,读书人的快慰跃然纸上。
中国古代的诗史埋伏着诸多丰富的思想,历史与哲学的话题亦不可胜数。顾炎武从诗中寻出历史的本然,废名打捞到缥缈的佛音,马一浮则悟出孔子诗学的核心之所。我看近来学人解析古代诗词的文字,觉得各取所需,得其要义而用之。从诗中看教化之用,是儒家审美的要点之一,但曾经因为道学家的滥用而多陈腐之气。不过徐梵澄以为,好的作品,的确有精神突围的意义,他对于陈散原、黄晦闻诗词的点评,就有孔夫子的遗音,在他看来,诗歌发之于心,得以流传,乃滋养世道人心的价值使然。
这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缺少宗教的民族,却在诗里承载了人间的智慧之语,那悠远的韵律比庙宇间的吟哦不差,也有神启的作用吧。但这需要对于词语的阐释与升华。古人的文字常常以小见大,在微言之中散出广远之气。我们读它,不仅仅懂得词语间的要义,还要深味人性的明暗。那些明察人间万象的人,对于古人的理解可能更深。
诗外文章,是个大题目,写好它的人并不多。好的诗,一是可感,二是可展。诗外文章就是伸展的部分。有时候我们不妨把散文、小说也看作是诗的余音,它们也沐浴在诗神的光泽里。托尔斯泰说自己的《战争与和平》是看了莱蒙托夫的长诗《波罗金诺》的产物,可见诗歌内在的原发性。至于海德格尔从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歌里发现哲学因子,且影响了自己的写作,那更是有趣的话题了。
作者简介: 孙郁,辽宁大连人,1957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鲁迅及现当代文学研究,主编《鲁迅研究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出版多部鲁迅研究专著,如《鲁迅忧思录》《鲁迅与陈独秀》《民国文学十五讲》等。代表作包括《鲁迅遗风录》《被亵渎的鲁迅》等。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朱自清散文奖、汪曾祺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