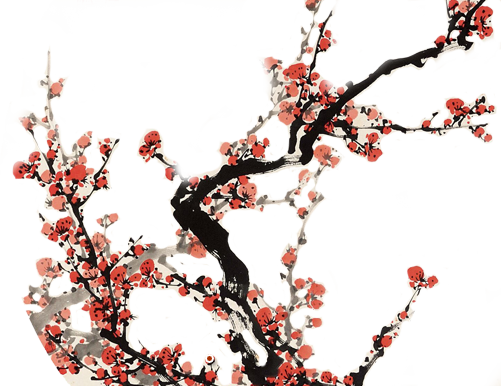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我的哥哥张耀千
张 冰(辽宁营口)
一晃儿,哥哥已经离开我们一百天了。一百个日夜,对于漫长的人生而言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失去手足的我来说,却是每一个刻度都浸满了思念。
从墓地回来的那天起,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流。在这无尽的哀思中,我不禁回望起我们张家那段充满血泪与坎坷的家族历史,回望哥哥那在苦难中顽强扎根、在风雨中长大的童年。
我的哥哥于1935年10月出生于营口市郊区江家房的王户屯,辽河入海口的风土赋予了他坚韧的品格。他的一生,是致力于革命、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岁月的长河中,他始终坚守信仰,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用“杰出共产主义战士”来称呼他,不仅是对他精神的高度概括,更是对他一生功绩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回望家族的过往,曾是一部辛酸而厚重的史书。曾祖父与祖父曾是那片土地上勤劳坚韧的创业者,他们凭着双手和智慧,拥有了百亩盐田,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辽东湾盐业商行”。那时的家族,盐堆如山,商贾云集,兴旺一时,是远近闻名的殷实之家。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东北,那片凝结着祖辈心血的盐田被强行没收,家族的脊梁第一次遭到重创。抗战胜利了,本以为苦尽甘来,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又以莫须有的“通共”罪名霸占了家产。一夜之间,家产散尽,家族彻底破产,繁华落尽,只剩下满目苍凉。
一九四六年的初春,寒风依旧刺骨。怀着对旧世道的满腔愤懑,也为了寻求一条活路,我的父亲带领着叔侄六人,毅然决然地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立下誓言:不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绝不回家!那是一种决绝的悲壮,男人们走了,把家族的生存重担全部扔给了身后的女人。
父亲参军后,我的母亲独自带着四个孩子在家熬日子。那一年,哥哥张耀千刚刚十一岁。本该是在父母膝下撒娇、背着书包上学的年纪,他却不得不早早地挺起稚嫩的肩膀。他身下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而母亲的怀里,还怀着七个月大的小弟弟,那是尚未出世的生命。那个年头,真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民不聊生。
父亲走后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成为了记忆中最黑暗、最惨痛的一年。那是闹饥荒最严重的时期,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饿死的、冻死的人屡屡发生,听母亲后来含泪讲起,左邻右舍的几个村几乎天天都在死人,路边、沟壑里,饿死的孩子随处可见,那惨状让人目不忍睹。
那年的初冬,寒风凛冽,外面飘着冰冷的雪花,家里却连一粒粮食都找不到了。六岁的姐姐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她躺在母亲的怀里,用最后一点微弱的声音喊着:“饿,妈,我饿……”母亲心如刀绞,却无计可施。年仅十一岁的哥哥到外屋的水缸里盛了半瓢水喂了姐姐。姐姐刚喝了一口,小小的身子猛地一抽,就咽气了。
那是怎样的绝望啊!当时哥哥饿得连走路都费劲,根本没有力气抱起姐姐,只好拖着姐姐的两条腿,把她埋在家里后面的土壕子里了。据哥哥讲,当时把姐姐的后脑勺的头发都拖掉了。那是他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那一年的冬天,也是国共两党进行殊死“拉锯”的时期。为了争夺营口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两军进进出出,炮火连天。周边的老百姓在夹缝中生存,更是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就在这兵荒马乱的当口,母亲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四哥就要临产了。哥哥看着日渐憔悴的母亲,流着泪说:“妈妈,咱俩不出去要饭,在家就得饿死。”母亲一把抱住哥哥,放声大哭:“大儿子懂事了。等妈妈生下你小弟弟后,我们娘仨一起走。”
一个月后,四哥降生了。那是一个在苦难中来到世间的生命,可迎接他的没有乳汁,只有无边的饥饿。家里已经没有一丁点可吃的东西了,母亲为了保住其他孩子的命,在生下四哥的第六天,便不得不忍着身体的极度疲惫及疼痛,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带上哥哥,一步一挪地离开了家乡,蹒跚向北逃生。
那一年,母亲才三十一岁。听母亲讲,当时天气极冷,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产后虚弱的身体根本抵御不住严寒,血水一直顺着腿流到脚后跟,冻得硬邦邦的。每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疼痛,那种痛苦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是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所能爆发出的最坚韧的意志。
走了一天多,母子俩终于到了大石桥。当时的大石桥火车站前,虽然人来人往,但到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有做买卖的,有赶集的,更多的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难民,有要饭的,甚至有卖儿卖女的……那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
大哥穿着破衣烂衫,因为长时间饥饿和劳累,终于支撑不住,饿得躺在马路牙子上,一动不动。一位赶大车的中年男子路过,用脚踢了一踢哥哥的脑袋,冷漠地问:“这孩子死了吧?”母亲急忙爬起来,带着哭腔说:“没死,是饿的。”那位好心的男子从车上的马槽子里拿出一小块豆饼递了过来。母亲把那块豆饼泡了些水,一点点喂给哥哥。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一口气来。
就在这时,我的一位远房表舅,名叫冷守成,也在车站前拉杂活。他看到了母亲这般悲惨的境地,看着怀里那个连哭声都没有的婴儿,便好心地劝母亲说:“妹妹呀,还是把怀里的孩子送人吧,让孩子找个好人家,有条活命吧。”
那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母亲的心里像被刀绞一样,想:“自己的亲骨肉,怎么能送人呢?”又想:“刚生下几天的婴儿,没有奶吃,早晚也得饿死。”在万般无奈之下,在表舅的反复劝说下,母亲只好咬着牙,把怀里抱着的四哥送人了。
四哥被抱走的那一刻,母亲紧紧抱着大哥,放声大哭。那哭声撕心裂肺,直冲云霄,围观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伤心落泪。那是骨肉分离的痛,是那个乱世加在普通人身上最残酷的刑罚。
离开了大石桥,母亲带着哥哥一直往北走。娘俩儿,破衣烂衫,风餐露宿,走一道、要一道,尝尽了人间的疾苦。
次年深秋,母亲带着哥哥一路讨要到了海城境内。一天傍晚,灾难再次降临,哥哥突然发起了高烧,不省人事。母亲吓坏了,把他抱到一家门前的大榆树下,绝望地用手扒下榆树皮,放在嘴里一口一口地嚼碎,然后喂给哥哥。过路的人看到这一幕,都摇头叹息:“这孩子肯定不行了。”
母亲哭着喊着,救救孩子,没有一个人应声。就在母亲求生无望的时候,村里的一位好心人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汤,颤颤巍巍地走过来,对母亲说:“大妹子,快让孩子喝了,看能不能救活。”母亲趁热把汤糊一点点喂进哥哥嘴里。过了好一会儿,哥哥终于动了动,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这也是老天有眼。经过母亲六七天的悉心照料,哥哥总算是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
一九六五年,省里组织全省四级干部进行农业拉练会,哥哥作为其中的佼佼者,随队一路考察。命运的齿轮仿佛在冥冥中转动,拉练会的路线偏偏经过了他当年随母亲逃荒乞讨时曾经到过的那个村子。
那天,春风拂面,杨柳依依,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进村子。哥哥一边走,一边仔细打量着周围的一草一木,突然,他的目光凝固了。在不远处,一棵苍老粗壮的大榆树静静地伫立着,枝头挂满了嫩绿的新叶。在别人眼里,这只是一棵普通的树,但在哥哥眼里,这却是生与死的界碑,是他生命中最绝望时刻的见证者。
那一瞬间,时空仿佛倒流,十八年前的惨象如潮水般涌入脑海。哥哥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踉跄着走到大榆树下,伸出颤抖的双手抚摸着粗糙的树皮,眼泪瞬间夺眶而出,继而放声大哭。
那哭声悲凉而凄婉,震惊了随行的所有人。省领导、同行干部,周围的村民都面面相觑,感到莫名其妙。一位省领导见状,急忙上前扶住哥哥,关切地问道:“耀千同志,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哥哥努力平复着情绪,指着那棵大榆树,用哽咽的声音,如实将他当年讨饭、病倒、在这棵树下濒临死亡的情景,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当讲到母亲绝望地嚼树皮喂他,讲到路人摇头叹息准备收尸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那不仅仅是哥哥一个人的苦难,更是那个旧时代留给所有中国人的共同伤痛。许多人的眼圈红了,有的甚至流下了热泪。
据母亲后来讲,哥哥拉练回来后,整整大病了三天三夜。高烧中,他时而呼喊着死去的姐姐,时而呢喃着讨饭路上的艰辛。这场病,不仅仅是身体的透支,更是积压在心底多年的童年与少年的心酸与苦辣的一次总爆发。哥哥的心情,是那些没有经历过生死边缘挣扎的常人无法理解的。那泪水里,有对苦难岁月的控诉,也有对新时代来之不易的感慨。
苦难是最好的老师,它磨砺了哥哥的意志,也坚定了他的信仰。全国解放后,哥哥深知新生活来之不易,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感激之情,他如饥似渴地走进了小学“速成班”学习。他倍加珍惜这迟来的读书机会,起早贪黑,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凭借着扎实的文化知识和突出的工作能力,毕业不久,年仅十九岁的哥哥就当选为江家乡乡长,成了远近闻名的年轻干部。二十三岁那年,区委为了锻炼年轻干部,将他调到了全乡最困难、最落后的城子村任党支部书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哥哥刚调任城子村党支部书记时,摆在面前的是一副烂摊子。村里所谓的耕地,其实大部分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这种地,旱天硬邦邦,涝天水汪汪,种什么死什么,真是“旱也不收、涝也不收”,村里的老百姓穷得叮当响。
哥哥到任后,没有丝毫退缩。他怀着一定要让乡亲们吃饱饭的朴素愿望,带领干部群众没白天没黑夜地干。修水利、平土地,他总是第一个下坑,最后一个上岸。然而,由于基础太差,尽管大家拼尽全力,老百姓的日子依旧艰难,还是只能吃糠咽菜。长期的劳累加上营养跟不上,不久,这个铁打的汉子终于累倒了,躺在床上起不来。
当时,母亲看着日渐消瘦的儿子,心疼得直掉眼泪。她带着病中的哥哥找到区委领导,含泪要求调转工作。母亲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实在:“孩子年龄太小,才二十出头,离家又远,这担子太重了,他承担不了这样繁重的工作,求求组织给他换个轻快点的岗位吧。”
区领导耐心地听完母亲的哭诉,并没有答应调动的请求,而是温和而坚定地做起了母亲和哥哥的思想工作。领导看着哥哥,语重心长地鼓励道:“耀千啊,作为共产党员,就要勇于挑重担。你想想,现在的苦和旧社会的苦相比,哪个苦?”哥哥愣住了,眼眶湿润了。领导接着说:“旧社会的苦,是吃不饱、穿不暖、被人欺压的苦,是真苦;现在的苦,是建设中的苦,是为了将来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的苦,是苦中有甜。为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再苦再累也不能退缩,这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啊!”
这一番话,像重锤一样敲打在哥哥的心上,也唤醒了他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回到村里后,哥哥没有再说一句累话,他重新振作起精神,看着窗外贫瘠的土地,暗暗发誓:不改变落后村的面貌决不罢休!
为了全力支持哥哥的工作,解除他的后顾之忧,深明大义的母亲与父亲商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全家从生活相对便利的江家房村,搬迁到了贫困落后的城子村。母亲说:“儿啊,咱全家都来陪你,咱们一起干,我就不信这碱地长不出庄稼!”
有了家人的支持,哥哥更是如虎添翼。在母亲的鼓励下,他与村里的干部群众一起,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会战”。他们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先将那些颗粒不收的盐碱地全部改为“台田”。所谓“台田”,就是挖沟取土,将田面抬高,利用沟渠排水淋盐,既能防旱,又能防涝。
在改造盐碱地的大会战中,哥哥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普通一员。他以身示范,不分白天黑夜,与人民群众干在一起。寒风刺骨的冬天,他跳进冰冷的泥水里挖沟;烈日炎炎的夏日,他带领大家筑坝。手磨破了,包扎一下继续干;肩膀肿了,垫上毛巾接着挑。经过一个秋冬的艰苦“大会战”,全村的盐碱地旧貌换新颜,普遍变成了既防旱又防涝的标准“台田”。
汗水没有白流,老天终于露出了笑脸。第二年,全村的粮食获得了好收成,那些曾经白茫茫的不毛之地,长出了金灿灿的庄稼。乡亲们第一次手里有了余粮,脸上有了笑容。全区特意在城子村召开了现场会,推广了建“台田”改土的先进经验,哥哥的名字也在十里八乡传开了。
然而,哥哥并没有满足于此。虽然盐碱地改为“台田”后,村里的贫困状况有所缓解,老百姓不再饿肚子了,但哥哥心里装着更大的目标。他看着乡亲们碗里依旧是杂粮窝头,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要彻底地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让村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吃上梦寐以求的白米饭。
于是,哥哥大胆地带领村干部到外地考察,学习种水稻的先进经验。回来后,经村两委班子慎重研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全村的“台田”全部改为水田,种植水稻!
说干就干。经过全村人民一冬天的奋战,挖渠引水,平整土地,昔日的旱地“台田”全部变成了整齐划一的水田,乡亲们期盼着来年一定能吃上白米饭的。
可是,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麻烦来了。原来,村里旱田改水田这么大的动作,区委竟然不知道,也就是村里没有及时上报。这在当时强调组织纪律的年代,可是个不小的错误。
于是,区里迅速组成工作组来到村里调查。工作组召开了干部群众大会,气氛严肃。会上,领导严厉批评道:“私自搞旱改水,既不上报、又不汇报,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是一种盲干行为!”接着,领导的话更加严厉:“如果这次旱改水不成功,造成了损失,将开除张耀千的党籍!”
这句话像一记闷雷,炸响在哥哥的头顶。哥哥参加工作以来,一心为民,兢兢业业,从没受过这样的打击和委屈。巨大的压力下,这个坚强的汉子一下子就病倒了,躺在床上,高烧不退。
母亲知道后,非常着急,也为哥哥捏了一把汗。她心疼儿子受委屈,更担心水田的成败。原因是,水稻是“水袋子”,必须有充足的水源。如果没有水,这几千亩水田将颗粒无收,那样的话,不仅哥哥的前途毁了,全村的老百姓跟着喝了西北风,怎么活呀?
那段时间,母亲整天守在田埂上,望着天空祈祷。或许是哥哥的诚心感动了上苍,也真是老天有眼。就在那一年,旱改水后的冬天,瑞雪普降,雪量很充足,给土地储备了丰富的水分。到了第二年春天和夏天,雨水也比较充沛,沟渠里水流潺潺,最适合水稻育苗、插秧和生长。到了秋季,又赶上天公作美,阳光明媚,昼夜温差大,正是晒米的好季节。
那一年的秋天,全村遍地金黄,稻浪翻滚。当年水稻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大丰收!全村的老百姓终于吃上了香喷喷、软糯糯的白米饭。那一刻,哥哥的病似乎一下子好了,他吃着香甜的米饭,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明白,所有的委屈和付出,在这一刻都变得无比值得。他与大家共同享受着胜利的喜悦,那是一份沉甸甸的幸福,更是一份共产党员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丰收的喜悦如同春风一般,吹散了之前的阴霾与误解。第二年,区里不仅没有追究哥哥的“过错”,反而充分肯定了旱改水的成功经验,在全区范围内大力推广,全区老百姓的餐桌上多了这来之不易的白米饭。从此。哥哥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广播电台里也时常传来他铿锵有力的声音。一时间,哥哥成了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成了农民心中的“米财神”。
然而,荣誉的光环背后,是哥哥透支的生命。认识和了解哥哥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能干事、并且能干成事的人,更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拼命三郎”。由于常年超负荷的劳作,风餐露宿,哥哥的一身病痛像影子一样甩都甩不掉。在我的记忆深处,哥哥曾做过三次手术,其中有两次是惊心动魄的大手术。最严重的一次,是针对他那积劳成疾的肺部进行的手术。那次手术,整个胸部都被打开,为了切除病灶,甚至无情地切断了两根肋骨。
那场手术是在鞍山的千山医院进行的。那一年,我才刚刚上中学,正值暑假,我便去医院护理了哥哥一些日子。医院的病房里,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哥哥术后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胸口的包扎触目惊心。即便如此,只要稍有精神,他还要和来看望的人谈论村里的农事。在那段日子里,我亲眼看到市委、区委的领导多次专车赶来看望哥哥。他们坐在病床前,握着哥哥的手,嘘寒问暖,那种发自内心的关怀和体贴,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那不仅仅是对一个干部的关心,更是对一位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付出了太多心血的好儿子的敬重。
时间来到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那是一个刻在骨子里的日子。营口、海城一带发生了强烈的大地震。那年我才十八岁,中学刚刚毕业。那天傍晚,地光闪过,山摇地动,死伤无数,一片末日景象。在那个惊魂未定的时刻,我亲眼看到哥哥在地震前后整天整夜不着家。他就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天天守在大喇叭前,向村民一遍遍宣传防震知识、叮嘱注意事项。他的声音沙哑了,还在喊,喊个没完,仿佛那声音能筑起一道抵御灾难的墙。
地震发生后,无情的震魔摧毁了我们家的房子,房倒屋塌,一片狼藉。可是,身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哥哥,在灾后的五天五夜里,竟然一次都没有回过家。他冒着余震的危险,挨家挨户地查看灾情,问寒问暖,组织人力帮助受灾农户搭建简易防震棚。年迈的父亲看着自家倒塌的房屋和满目疮痍的院子,听着外面广播里哥哥嘶哑的声音,气得浑身发抖,在家里大骂道:“这个小子,心里只有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这个家!”
虽然父亲骂得狠,但心里其实明白儿子的为人。正是由于哥哥的认真负责和辛勤工作,这场百年不遇的大地震中,全村几百户人家,竟然没死一个人。这在当时堪称奇迹,哥哥也因此得到了上级和中央慰问团的高度嘉奖。父亲的骂声里,何尝不是带着一丝心疼和无奈的骄傲。
哥哥的一生,心无旁骛,一心想着群众。为了老百姓,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半点私利。他在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区委几次看中了他的才干,想要提拔他到区里工作,如任农委主任、农业局局长、经济部部长等重要职务。面对这些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升迁机会,哥哥都一次次推辞了。他总是憨厚地笑着说:“我离老百姓近一点,能直接为他们服务,心里才踏实。”他舍不得离开那片土地,舍不得离开那些视他为亲人的乡亲。
哥哥在工作能力和为人处世方面无可挑剔,而在为政清廉、两袖清风方面,更是所有领导干部的榜样。他当了四十多年的领导干部,手过财,眼过物,却始终保持着一颗金子般干净的心。集体的财产,他一点儿也不占;集体的钱款,他一分也不花;遇到有便宜的事儿,他一点儿也不贪;群众送的礼物,他一个也不收。
记得哥哥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大侄女,在部队是一名优秀的医生。转业回来时,按照当时的政策,只要哥哥这个当书记的父亲开口打个招呼,找找人,就能顺理成章地分配到条件优越的区医院工作。可是,哥哥就是咬紧牙关,坚决不说话,不肯动用这点特权。结果,我那个懂事的侄女,只好被分配到了离家十多公里以外的乡下卫生院工作,每天风吹日晒,奔波劳碌。对此,哥哥从未有过一丝后悔。
还有一次,哥哥到外地去开会。回来报销时,我发现那张住宿发票被他撕掉了,碎屑扔在纸篓里。我惊讶地问他怎么回事,他淡淡地说:“这次会议安排的住宿,费用稍高了一点儿。虽然符合规定,但咱们村里还不富裕,如果报销了,影响不好。”这种近乎苛刻的自律,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傻”,但在哥哥看来,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每到春节,东北农村的习俗是要杀年猪过大年的。那时候物质相对匮乏,周围的乡亲们为了感谢哥哥一年来的帮助,免不了要送来一些热气腾腾的杀猪菜、新鲜猪肉等。但每次送来,都会被哥哥板着脸让家人给退回去。那时候,我时常要充当他的“跑腿人”,一趟趟地把东西送回去,还得替哥哥说好话。哥哥常说:“咱们是干部,不能吃老百姓的东西。一口肉事小,失了民心事大。”
哥哥的这些心思,只有我最理解。他之所以如此努力工作、迎难而上;之所以为民服务、心系百姓;之所以两袖清风、无私奉献,都是为了报答党的恩情。他常私下里对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张耀千,更没有我能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是党把我从旧社会的死人堆里救出来的,我这辈子都还不完。”这份朴素的感恩之情,成了他一生前行的不竭动力。
哥哥退休后,我很惦念他。虽然我自己工作也比较忙,平时很少能抽出时间回乡陪他唠唠嗑、说说话儿,但心里总是挂念着。但我每次见到哥哥时,都会把兜里的整钱全部掏出来塞给他,虽然他总是推辞,但我知道那是弟弟的一份心意。记得有一年,哥哥喝好了我送他的纯粮散白酒,赞不绝口。第二天,我特意跑到市里的永红市场,把那个摊位的两桶白酒全包了,雇车送到哥哥家,让他喝个够。可惜后来,哥哥患了脑血栓,为了保命,不得不滴酒不戒了。看着他面对酒菜只能摇头的样子,我心里一阵酸楚。
哥哥患病后的日子,我很痛心。回首他的一生,真的是太苦了。童年丧亲、少年乞讨、青年劳累、老年病痛,这一辈子遭的罪太多了,到了晚年,也没能享受几天清福。
哥哥病危的那几日,我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了。不知道背地里流了多少泪,甚至怨恨苍天无情,总觉得老天对哥哥不那么公平。为什么要让这样一个好人承受如此多的痛苦?
一晃儿,哥哥离开我也有一百天了。一百天的日日夜夜,思念如野草般疯长。我想,故去的哥哥,还有那些早年间不幸离世的姐姐、妹妹,他们一定会在另一个世界重逢。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找到那受尽一生苦难的母亲,如果找不到,慈爱的母亲也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因为,有妈妈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天堂。在那里,没有饥饿,没有寒冷,没有病痛,只有团圆和温暖。
哥哥,弟弟想念你……
作者简历:张冰,辽宁营口人,字耀松,笔名东南。作家、学者、诗人。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一级散文家。先后担任中学语文教师、营口市直部门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曾任营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市诗词学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中国乡土文学家协会理事、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理事长、关东十三友成员。现已出版诗集、散文集五部,主编学术研究专著1部。其中散文集《芦苇》获辽宁省二十世纪“丰收杯”三等奖、中国乡土文学奖。其传略收入《中国当代艺术名人大辞典》《中华人物大辞典》《中国人才世纪献辞》《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等10余部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