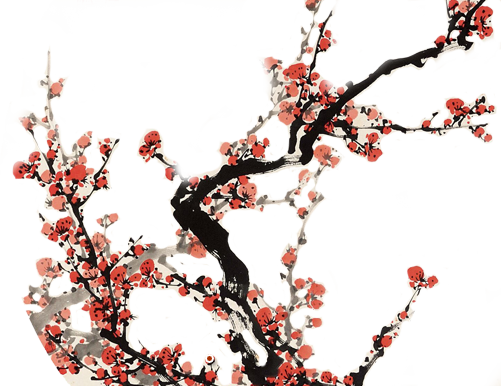花 凋
沙 爽
一
现在我们看她,真的像看一朵浮在水面上的花。时光的花瓣如此层叠交错,使裹在其间的花蕊接近一个朦胧的梦魇。这个没有根须的女子,如果不是史书上的记载确凿,我们甚至很容易就把她错认为一个传说。
有一个与历史有关的设问是这样的:对于沉浮在历史这条大河中的人物,我们应该怎样计算出 他们在后人心中真实的影响力或曰知名度?答案也许可以用现代数学展示:在纸页上画出两条数轴,如果X轴可以设定为“质”,也就是他(她)留在世人心底的深刻程度;那么Y轴就应该是“量”,指向他(她)流传下来的故事的数目。而如果他(她)碰巧是个诗人,那些在世人心里留下印迹的诗句也理应加入其中——这样一路算下去,简单的算式难免又演变为一门多维度的复杂课程。
不错,她就是这样一个难以用质和量进行简单叠加的人——她留给后世的诗歌,比较有名的只有一首七绝和半首词;另外还有一阕描写她的词,因为写得又高雅又香艳,一不小心,就让她的美丽也成了经典和传奇。
但是直到今天,人们连她的真实姓氏也未能弄清楚。这算得上是一件奇怪的事:《全唐诗》里明明收录了她写的一百五十多首《宫词》,却没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更不用说家世。
也许这是因为:她是一个亡国皇帝的妃子。
因为她是一个亡国的妃子,才留下了这么一首著名的《述亡诗》:
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二
入宫的那一年,她十六岁。作为皇帝的他,后蜀之主孟昶,二十三岁。
依我看,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年龄落差。有一点距离,但不妨碍彼此成为知己。如果落差再大一些,年长的一方就会不自觉地生出些居高临下的意思。虽然仰望也能诞生美感,但在男人这一边,多数时候,需要以对对方的尊重来延长爱意缱绻的时间——从此后二十三年里发生的故事来看,他们之间的感情,确实很有些在皇帝与他的嫔妃之间罕见的相濡以沫的意味。
她不是他的第一个爱人。在她进宫之前,他极其宠爱的张贵妃,在登山赏玩时受雷电惊吓而死,让人疑心这不幸的美人可能患有先天心脏病之类。他当然悒郁不乐;于是她被从民间筛选出来,作为献给他的安慰品。
史书上说她原姓费,是歌妓出身。又有的说她姓徐,父亲是蜀地才子徐匡璋,后来家道败落。不管怎么说,她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这一点是肯定的。一个没有更多选择余地的小女子,意外地被选进皇宫,又意外地获得皇帝的宠幸——后宫佳丽三千,即使天生容貌出众,但要想集三千宠爱在一身,多少要靠老天的额外眷顾。她当年肯定这样想过。因为从她的那些诗里看,她在蜀地的生活算得上相当满足、单纯和快乐。
是的,因为单纯,所以快乐。
幸福在她,原本就是意外的天赐,没有必要苛求得太多。他宠爱她,这已经足够。后宫的嫔妃加上宫女,总有数千人之多,这些可都是她潜在的情敌,但她看她们的眼光是温暖而善意的,带着些许欣赏和赞叹,带着些许同情与爱怜。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因为诗歌无法说谎。虽然有的人以为文学可以作为人生的修辞,但是对不起,这些想借用文字美化自己的人最终打错了算盘。因为文字应该是从人的心里流淌出来的液体,它带着写作者的气息和体温。
月头支给买花钱,满殿宫人近数千。
遇著唱名多不语,含羞走过御床前。
诗有点直白,这也符合她简单的天性。但是你看看,这个皇帝是不是个没正经事儿干的家伙——居然亲自跑来给几千个嫔妃宫女发放“买花钱”,从他那挥金如土的奢侈天性来看,恐怕此举并非为了省下出纳以节约开支,而是他觉得这件事相当好玩——这满目的环肥燕瘦,满耳的环佩叮当,他心里一定油然生起无限丰足和饱满吧?作为他最宠爱的妃子,她肯定不必排在这个等候的漫长队列里,她应该是坐在他的身边,做一个乐在其中的旁观者,看着那些宫女们一个个地从面前走过去,娇羞可爱的样子让她喜欢。
在她的诗里,从来只有这些和众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欢喜,没有顾影自怜的凄凉和幽怨。一个觉得自己幸运的女人,她乐于宽厚也乐于施悯。
因为这宽厚,她成了一个与别人不太一样的女人。
她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没听说她请夫君皇帝把娘家的谁谁弄进朝廷,做个什么什么官。如果那样,也不可能让大家连她的姓氏都搞不明白。
如果一定要深究,我认为富有忧患意识的女人其实大都缺乏安全感。一定要居安思危:将来他不再爱我了怎么办?所以赶紧趁着有能力的时候拼命敛财,再修筑一个足够坚实的政治后台。男人的爱总之是靠不住,要及早用自己的双手积累起后半生的繁华铺垫。
相比起来,她差不多是个缺心眼的女子,只知道及时行乐享受过程,却不去想一想无处着落的黯淡未来。但是世事就这样奇怪,这个没有过去也没有建设好未来的女人,被据说是最朝三暮四的职业皇帝宠爱了整整二十二年。
她是他的“慧妃”,没有史料提到他是否还有一位皇后,但即使这个皇后存在着,显然也没有对她构成什么压力。她没有想当皇后的奢望,因此也不觉得仅仅做个贵妃有什么可悲。直到后来她进入大宋后宫,太祖赵匡胤一度有过立她为后的想法,但被宰相赵普以“亡国之妃,不堪母仪天下”为由劝阻,她也不以为意,反而向赵匡胤毛遂自荐,愿为册立宋皇后的国家级大型典礼担任舞台策划,同时负责谱曲和舞蹈设计,并做得相当成功。放在今天,她是那种不争抢不嫉妒,努力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的优秀中层干部。
三
姓名:不详
笔名: 花蕊夫人
性别:女
职业:皇妃
爱好:写作、骑马、射箭、踢足球
特长:烹饪、音乐、舞蹈、绘画
……
单看这个履历表,今天的女人就要倒吸一口凉气。社会在进步,没有女人肯承认自己的本事比前辈们退化了。以眼下的标准,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已经大抵称得上女中极品;如果还侥幸长了一副好模样,那更有百分之二百的理由敝帚自珍。如今在社会上混碗饭吃有多么不容易,女人们哪一个不是抖出了全部精神?会打字会发传真会做文案还只是基本功,还得会哭会笑会跟老板周旋跟客户套瓷。就算撇开辛苦的工薪族不做,自由职业也同样需要手艺和资本。我认识一位八零后的漂亮女孩,说穿了就是给一位港台富商做“二奶”,不过这女孩的“二奶”做得还算用心和专业,因而被商人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极口称赞。只要商人没有应酬,女孩便亲自下厨炒菜做饭,虽然都是些简单的家常菜,却让富商享受到了天堂般的家庭温暖。其余的时间,女孩用来美容购物打麻将旅游观光,让她的昔日女伴们羡慕得眼珠发蓝。现在的社会分工精细到这般地步,男人们还有谁敢指望在自己家里欣赏到专业水准的现场歌舞表演?
如果仔细清算一下,这个孟昶虽然称皇称帝,他的小帝国却只局限在四川那一小片区域。他的老爸孟知祥作为唐庄宗李存晶的堂妹夫,以西川节度副使的身份入镇西蜀,后来自立为帝。放在今天,这父子二人也就是个省级一把手。而贵妃也不过是古时候“二奶”的合法别称。这么一路换算下来,做个一千年前的女人,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如果说骑马踢球还可以算作娱乐加锻炼身体,那音乐、舞蹈和绘画可都是专业技术,更别说烹饪——别看女孩子小时候都喜欢过家家游戏,好像一个个天生就准备好做贤妻良母,真要让她们围着锅台转上一辈子,没有哪一个不喊冤叫苦。而且,烹饪虽然是比较世俗的艺术,却和音乐绘画一样,入门需要苦功,成就需要天赋。如果不仅能做到色香味俱佳,还能独树一帜,那简直是艺苑奇葩。
和现代派八零后女孩的家常菜路线不同,花蕊夫人走的是出奇制胜道路。最有名的是“月一盘”和“绯羊首”两道菜。雪白的羊头加入红姜炖熟,紧紧卷起,用石头镇压,腌进老酒,使酒味入骨,最后切成纸一般薄的肉片,装盘上桌,是为“绯羊首”。将山药切片,用莲粉拌匀,加以调味,清香扑鼻,味酥而脆,又洁白如银,望之如月。千年前一个女人的灵犀一点,竟使得“月一盘”就此成了山药的别名。
至于写作,是所有的功课中最省力气的。也可以说,诗是闲着没事时写着玩的。这一说,诗人们听了难免要生气。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她的诗从不引经据典,看不出什么学问高深。只因唐朝的王建老先生写的一百首宫词读来有趣,于是她也模仿着写起来。这世上有的事本来轻松明快,怕就怕有的人太煞有介事。至于因此而才名远播,在她,此事纯属意外。
四
好像所有轻松明快的时光都是短暂的,喜庆的鼓点总是刚刚敲响就转调作悲凉的唢呐。十四万蜀军抵不住大宋的数万兵马,对着惶惶无计的满朝文武,孟昶长叹一声,出城纳降。
这是公元965年农历二月十六,元宵节刚过一个月,蜀中成都春意甫至。还是前一年春节,他在迎春的桃符上写下一副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还在四年前,即公元960年,赵匡胤曾下令,将他自己的生日,即每年的农历二月十六日,定名为“长春节”。孟昶降宋之时,不早不晚,恰是“长春”之日。而赵匡胤派往蜀地接管地方事务的,正是一个名叫吕余庆的官员。
——这是天意?是谶语?还是人间离奇的巧合?
他们被宋军“护送”,前往汴京,接受大宋皇帝封赏。但他和她所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他南下经长江水路,由峡门赴开封;而她则独独北走剑门,经关中入汴京。途经葭萌关,她形单影只,容颜憔悴,在驿站的墙壁上题下这首《采桑子》: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声声闻杜鹃。
刚写完这四句,军骑便来催促她上路。真个是国破家亡,来程杳然,去路也半点由不得自己。
因为这首词当时未能写完,后来便有好事者替她续出了下半阕:
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我想,无论哪个女人看了这天外飞来的后半阕,都会有一股气从脚底直窜上来。怎么可能不生气?这些没有见识的男文人啊,干点儿什么事不好,偏要跑来这里卖弄风骚,并且,自以为极尽聪明和华丽地,用狗尾巴续上貂。
她已经三十九岁了。在后蜀宫中度过的二十二年优裕生活,回顾起来直如一缕青烟。在漫长的押解朝圣路上,她度日如年。身为案鱼俎肉,她怎么可能对一个遥远国度里敌对的帝王,心存憧憬和绮念?
但是,她心里是有某种预感的,这非同寻常的独走陆路已经透露了某些信息。谁都知道水路轻捷但是暗藏险恶,那个从未谋面的大宋皇帝赵匡胤,为什么居然把她的小命看得比她的皇帝夫君还要贵重?
也许她的担忧是多余的,当他们这些亡国的君臣先后抵达开封城外,大宋朝接待的礼数一点儿也不轻慢,甚至可以算得上相当隆重铺张。《宋史》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场面:
“昶将至,命太宗劳于近郊。”由当时大宋的第二号人物、晋王赵光义亲自出马,一直迎接到郊外,规格不可谓不高。
“昶率子弟素服待罪阏下,太祖御崇元殿,备礼见之。”胜王败寇,昔日里独自逍遥的后蜀皇帝,今朝不得不做了大宋的臣子,受封为秦国公、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赵匡胤出手大方,“赐昶袭衣、玉带、黄金鞍勒马、金器千两、银器万两、锦绮千段、绢万匹;又赐昶母金器三百两、银器三千两、锦绮千匹、绢千匹;子弟及其官属等袭衣、金玉带、鞍勒马、车乘、器币有差;又遣使分诣江陵、凤翔赐其家属钱帛,疾病者给以医药……先是,诏有司于右掖门外,临汴水起大第五百间以待昶,供帐悉备,至是赐之,又为其官属各营居第。”从孟昶本人至其家属,以及旧属臣僚,一律重重赏赐,加官晋爵。如此一来,大宋国宽厚仁义的美名声震天下,那些还没有前来归附的小朝廷,眼看着势单力薄,是拼死抵抗,还是来与大宋国共享千秋富贵?赶紧做个决断吧。
但是该来的还是来了。当着这许多人的面,他小小地将了她一军:听说花蕊夫人诗名素著,今能否赋诗一首,就述这蜀亡之事,如何?
她在心里冷笑一声。他想要她的什么态度?她缓缓低首,让他看见她的温婉和无辜。然后她抬起眼睫,他暗暗吃了一惊,那温婉的后面分明是峥嵘的硬度。她不疾不缓,不卑不亢,吟出了那首著名的七言绝句。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那前朝后代被指为红颜误国的美人们听了,也都会跟着舒一口淤积在心底的恶气吧?
但是你再细看,就可以看出她些微的心思。她不去歌颂他的伟绩——那算是什么伟绩?不过是一个男人的虚荣和膨胀的野心。但是她也不去揭破。用一根隐喻的针,刺出他隐喻的血,那对她有什么意义?所以她只管说她自家的事,仿佛这件事与他毫无关系。激怒他会带来什么好处?她一死了之又能挽救什么?
而且,更重要的,她并不想死。
五
她不想死,因为她不喜欢疼痛。她喜欢轻盈、欢快、喜悦,以及诸如此类的词。死亡是一件多么苦痛的事,身既疼,心也疼啊。她爱她自己,她也爱活着这件平凡的事。
能平凡地活着也是幸福的,好过不平凡的死。何况是活在这样一个美丽而健康的身体里。不是每个灵魂都有这样的幸运,在人间依附进如此完美的肉身。有多少灵魂对囚禁它的身体满怀敌意却苦于无法脱困——它不满意它的容貌、高矮、胖瘦;不满意它头发的光泽、鼻梁的高度、皮肤的颜色;不满意它说话的声音、走路的姿势、接人待物的风韵。灵魂苛求完美,而肉身永远存在缺损。即使长年生活在深宫内苑,她还是看到了这么多人间的挣扎和不甘。那个羡慕她骑马驰骋的小宫女,笨手笨脚,上了马抓不住缰绳,只会抱紧马鞍不放,最后对自己整个地丧失了信心;那个喜欢钓鱼的高妃,只不过受了一点凉,就再也没能爬起来……而她呢,她已经三十九岁了,如果不是上天的格外恩宠,她怎么可能仍然如此鲜活而饱满?
这么好的身体,她有什么理由不加以珍惜?她有什么理由执意让它死?即使它只是个美丽的皮囊,很容易讨得男人的欢心;然而她自己,比男人们还要珍爱它十倍。
还有,谁知道她的心里是不是藏了又一声冷笑呢——她倒是想看看,如果她不主动投进死神的怀里,命运到底会拿她怎么处置?
他们总说“诗无定解”,即使这么一首坦率得近乎俚俗的诗,也可以分解出多种解释。在赵匡胤这儿,他理解为是她婉转抛来的橄榄枝。散朝后回到寝宫,他反复玩味着她吟咏的那最后一句:宁无一个是男儿,宁无一个是男儿……那蜀地的十四万兵士,当然其中也包括孟昶和他的臣子们,竟没有一个是铁骨铮铮的男子——她是在暗示他,只有他这个征服者,胜利者,才是真正的顶天立地的男人!
这一刻,他心花怒放,豪情的小闪电噼里啪啦地四下里乱溅。
他想到她的美,比那些口口相传的形容词还要耀眼十倍;他想到她可人的小聪明,竟以这样的方式向他递出了磊落的赞美。到了这个时候,昔日里那个思虑周详的帝王彻底消失,他变回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脑子里的骏马只朝着那个意愿的方向一路飞奔。这样一来,她无奈的低首原来满怀哀怨,她有意无意的一瞥贮藏有万千召唤。她在他的心里幻化成一株楚楚可怜的曼妙茑萝,而她藉以安身立命的那株大树业已訇然倒塌——现在,他还怎么忍心看着她与那棵枯萎的朽木一起倒下——也罢,此木既已无用,就让它永远从人间消失吧!
七天之后,时年四十七岁的亡国皇帝孟昶,因“水土不服”,在大宋皇帝特地赏赐给他的深宅广厦里,暴病身亡。
众所周知,后世的史学家对赵匡胤多有偏爱,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人情味的帝王之一,并列举出许多实例作为佐证。比如他保全柴氏后人,不加农田赋税,对胆敢冒犯天威的人也真正做到宽宥大度。不仅如此,史学家们认为宋太祖的人格魅力几尽完美:心地清正;嫉恶如仇;虚怀若谷;好学不倦;勤政爱民;严于律己;不近声色;崇尚节俭;以身作则……把这么多好词同时奉送给一个人,这简直不像一向刻薄的史学家们的做派。既然有这么多案例树立起宋太祖的光辉形象,孟昶的猝死之谜,只能称为悬案一桩。
孟昶既死,他的母亲李氏不饮不食,三天后也平静地死去。
隆重的葬礼过后,花蕊夫人进宫拜谢皇恩。于是试图为太祖辩解的史家们开始有点说不清了——这个似乎并不酷爱女色的赵匡胤,的的确确,把花蕊夫人留在了他的后宫里,做了他的爱妃。
当然也可以把太祖的所为理解为对弱者的同情和怜惜——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弱女子,身离故土,夫君和婆婆相继故去,倘若身边没有一把足够强大的保护伞,几乎相当于羊落狼群——但是这样的理由,联系起宋太祖此前此后爱惜羽毛的处世基准,似乎多少有点儿牵强。
唯一的解释是:当一个男人一心只想得到他心仪的女人,他可以抛开这个世界,包括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目光和口舌。
六
几乎所有后世的记述都试图证明一件事:他待她简直太好了。但是没有人提到那对她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生活在这个繁华幽深的大宋后宫,她快乐吗?
那曾经的世界已然消散。那曾经的轻盈、散淡、心无挂碍,再也不会回来了。这皇宫不是她在蜀国的皇宫,她注定只是这里的客人,因为忘不了那被威压后不得不低下头去的命运。一个人的爱怎么可能缝合起头顶上一大片破碎的天空呢——何况,那是一份来自帝王的爱,本身就不可能纯粹和完整。
她想念那些远逝的时光,因为自知再也无法回头,这想念变得愈加痛楚和无望。失去的往往也是最好的,即使她努力做到平和豁达,但还是有一部分的她,落进了造化给人间设下的小小圈套。
她一遍遍怀想那个突然远去的帝王。他是个多么热爱享乐的人啊,如果没有意外,他本可以这样快乐地度过一生。可惜他是个皇帝,作为皇帝,他要么学会吃人,要么被人吃,老天没有留给他第三种可能。他给了她二十二年美妙的时光,这时光里聚集了她生命里几乎全部的重量。她想他对她近乎无限度的宠爱。她痴爱牡丹,又喜欢红色的栀子花,他就差人四处筛选优良品种,不仅在皇宫里开辟“牡丹苑”,还让民间也广泛种植,使得成都真的成了“锦城”。他还笑向她说:“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今后,试看‘蜀地牡丹甲洛阳’!”
而且,她隐约地想到,如果不是因为她,他也许就不会死;至少不会死得这样早。
她悄悄绘制了一幅他的画像,暗地里焚香为他祝祷。不料有一天她刚刚把画像张挂起来,赵匡胤提前下朝,仓促之下,她不及细想,只得谎称画像上的人乃是张仙,职司送子。五代时民间传说,有一个张仙人,俗名远霄,在青城山得道。她自幼长在青城,当然知道这个典故,便临时拉过来救急。可是因为她这几句话,后世便以讹传讹,都说张仙送子。那想要生儿子的人家,便都去求了“张仙”的画像来,供奉跪拜。
哎,有多少神灵,就这样顶着一张别人的脸,游走在这啼笑皆非的人间。
也正因为这个小小插曲,后人便有诗说她是“一点痴情总不泯”。
她“痴情”吗?
现代汉语词典对“痴情”的解释是:痴迷的爱情。可以理解为“对爱情达到痴迷的程度”。那甘愿变成望夫石的女人是痴情的,双双化蝶的梁祝也是痴情的,这样一想,痴情的人似乎都有一个悲剧式的收梢,因为痴情的人不计得失也不计结果。“痴”是迷醉,是忘我,而她即使再沉醉,心底总有一小块园圃永远醒着。她实在太爱她自己了,以致不能“痴”得彻底和决绝。
好吧,既然别人一定要说她“痴情”,那么“一点”也就够了。别“痴”得太深,丢失了自己,又拿什么去爱人?而如果连这一点痴情也无,那也不配说爱了。
然而此刻,我却想到了另一件事。所有人都说赵匡胤相信了花蕊的解释,特许她另辟静室,供奉这位送子的“张仙”——好像这个皇帝当真那么易于哄骗。谁都知道他见过孟昶,而且不只一次。除非那张画像画得太失水准,一点儿也不像孟昶本人,否则赵匡胤怎么会看不出来?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个男人,他可是那个发动陈桥兵变,而后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
作为一个开国的君主,他当然必须具备超出常人的勇气和智慧;而这智慧表现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装傻充愣,假装糊涂。
作为男人,我是说稍微有点智慧的男人,让真心喜欢的女人尴尬,那自己脸上又有什么光彩?
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同是男人,而且同是做皇帝的男人,表达爱意的方式并不一样。在孟昶,用的是“宠”;而在赵匡胤,用的是“宽容”。
如果一个女人足够聪明,她会知道:宽容,是更高一层的“宠”。
七
她想活,但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在她,终于也不能够。
她的死在民间被传得扑朔迷离。总的来说,宋末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的记述,应该是距离真相最近的。说的是花蕊夫人归宋后,赵光义也十分喜爱她。一次从猎后苑,花蕊夫人在侧,赵光义“调弓矢,引满拟兽,忽回射花蕊,一箭而死。”
蔡绦是宋代权臣蔡京的儿子,蔡京曾先后四次任相,在位共达十七年之久。蔡京为徽宗朝中太师之时,已年老体衰,视力也很差,诸多事务便悉数交于蔡绦裁决。宋钦宗即位后,蔡京因贪渎罪被贬岭南,蔡绦亦随之流放到白州。铁围山正是白州境内的一座山,位于今广西玉林西。而其时距离赵匡胤时代,仅百年余;蔡绦又是这样的一个特殊身份,他所记述的事件,当然比那些只会给皇帝脸上贴金的宋代史官要真实得多。
但是问题出现了:既然赵光义对花蕊夫人“十分喜爱”,为什么却要杀死她?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不知此前有没有人注意过。那就是孟昶和他的家眷臣属将到汴京时,赵匡胤曾命“太宗劳于近郊”。也就是说,在赵匡胤见到花蕊夫人之前,赵光义已经抢先一步,目睹了她的美貌。
不过,还有一个细节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年她已经年近四十,而他,刚满二十六岁。
情形有点诡异。他真的会爱上她?出于什么心理?
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一个三十九岁的女人,也已经算不得年轻了。除非她有张曼玉和赵雅芝那样的幸运,人到中年容颜未衰,反而在岁月的滋养下愈发清澈华美。蜀地气候温润,加上一千年前的纯净空气和绿色食品,再加上多少年如一日的优裕生活,还有她自己的乐观性格与日常锻炼,比真实的年龄年轻上十岁八岁是完全可能的。据说驻颜有术的女人需要同时具备安定的生活和不安定的内心,后者可以理解为丰富的内心与精神生活,那么这两点她也都具备。问题是她究竟有什么好,让三个先后都做了帝王的男人一见倾心?
不知在千年前的男人们眼中,什么样的女人最有魅力,现代版的魅惑女人据说要具备八种要素:健康、智慧、独立、优雅、风情、平和、率真、美丽。要求一个活在宋代的女人像今天一样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显然有违常理,但是不妨理解为精神上的独立——既已拥有以上的八样法宝,在千年以前,她在男人的眼中已经堪称十全十美?
缺什么就想什么,这几乎是人间至理。孟昶虽然久习诗文,却才华平平;赵氏兄弟系武夫出身,但都酷爱读书,奈何“稍逊风骚”。那一点会写诗的才华,在她自己看来只道是寻常,他们却因此认定她非同等闲。
有才华的女人大多以才华自恃,性情尖锐孤高,但她从来就没有把写诗当作一件值得标榜的事,好像一个人怀揣珍宝,奇货可居固然没什么不对,但处之泰然,更让人生出敬意。
至于这个赵光义,我们也可以约略窥见他隐蔽的内心——他的嫉妒,不仅仅缘于他喜爱上这个女人。甚至,那也不仅仅是爱,还有迷惑、好奇,还有对一个自信的生命强烈的征服欲——她曾经属于另一个皇帝,这其间的征服,充满胜利者之外的象征意义。
当年他与其他人一起,拥戴他的兄长黄袍加身,内心里更多的是期待和欣喜。那时候他还太年轻,只想到有一个做皇帝的兄长将会带来的光明前景。但是现在,他已经尝到了权力的个中滋味,知道作为“晋王”和作为帝王相隔有如云壤——即使是一奶同胞的兄弟,他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名字从“赵匡义”改成了“赵光义”。如果说改名还不算什么,那么这个女人,他先行爱上了她,却始终只能做一个“外人”。她袅娜的身影在最近的距离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都在提醒他的失败。他嫉妒的湖心里开始浮起恨的影子——既然这是一块永远无法握在自己掌心里的玉,不如干脆让它碎成瓦砾。
还有,他也想看一看,这个惯会假仁假义的皇兄,到底会拿他怎么处置——他杀死他的女人,并且理由充分——这女人是祸水,耽搁朝政——他难道会拿他抵命?或者为了一个女人责骂他?那么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个叫赵匡胤的人有多虚假。他生病的时候,这个皇帝哥哥还亲自为他用艾草热灸,怕手艺不精烫疼了他,还要先在自己的身上试验几下……他猜得一点儿也没错,他的这个兄长已经知道他眼下的势力有多强大,他一箭射死了他的女人,他居然神色如常,连眼睛也没有眨一下。
正因为他连眼睛也没有眨一下,他反而感到了害怕。这个男人,他的心太深,即使是做他的弟弟,他还是要加倍地小心。
直到十二年以后,赵匡胤病重,他的弟弟才终于找到了机会,并且也让史学家们怎么也抓不住他弑兄篡位的把柄——“烛影斧声”成了解不开的千古之谜。
八
被人爱不一定就是有福的,因为要看爱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幸被赵光义这样的男人爱上,就只能“可怜花蕊飘零,早埋了春闺宝镜”。
这个赵光义,从他后来强奸小周后,毒死南唐后主李煜,而小周后也不知所终这一系列事情看,这个男人不仅全然没有乃兄的风度,也不懂得什么是珍惜,什么是尊重。遇到他,只能是女人的一场噩梦。
你以为男人因为得不到你而爱极生恨,是真的太爱太爱你?你错了,他原只不过要借用你,来好好地疼爱他自己。
然而美人何辜,香消玉殒,只因怀璧其罪。
时间转眼过去了一百年,有个叫苏东坡的人,听说了花蕊夫人的故事,还有当年孟昶在摩诃池上的水晶殿前为他心爱的女人写的一首词。可惜时光荏苒,转述者只记得词中的开头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于是这个叫苏东坡的大才子略一沉吟,补作了全词,这首词自此流传千载: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那楠木为柱,沉香作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的水晶宫殿呀,夜色清透,四围花树暧昧,红桥隐隐。他和她酒至薄醉,相依而坐。他轻轻地握着她的手,听宫外鼓敲三更,暗香徐来,玉绳低转。只是: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