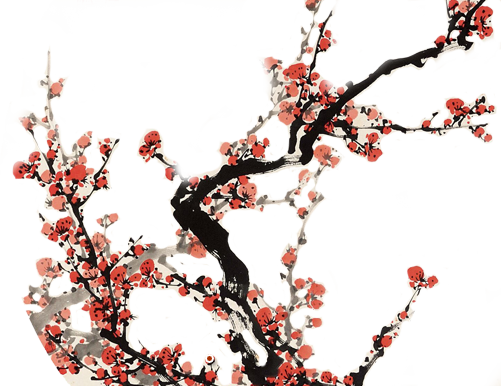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一个人的村庄
冯 伟
鸡叫头遍的时候柳婆就醒了。在这里这么多年,鸡叫是她唯一起床的号角,柳婆的心里没有钟的概念,只有鸡,再就是太阳了。她知道鸡叫头遍天就要亮了,鸡叫三遍太阳也就该出来了,大山里就是这样,一切都很准时。在柳婆的眼里那太阳不是自己出来的,是鸡用那一声声洪亮的啼鸣给呼唤出来的,那太阳就像鸡下的蛋,鸡一叫就出来了,红红的圆圆的鲜亮亮的一个“大蛋”。
柳婆起了身,天已经大亮了,但太阳还没有出来,这时的沟筒子静得清新,瞅哪儿都水灵灵的,整个山山岭岭沟沟壑壑就像夜里经过了沐浴,把前一天的灰尘洗掉了,湿漉漉地展现在柳婆的面前。
柳婆先是把鸡放了出来,每天都这样,不管怎么急,鸡一定要先放,她不能亏待鸡,这些鸡是村里人留下来的,多少只她也没数过:大芦花,小珍珠,白牡丹,黄杏仁儿,好看着呢。这些鸡被柳婆养得很肥,亮亮的毛身,肥大的形体,看上去就知道侍侯得应时,像一只只短尾凤凰,精神着呢。
鸡一只只走出了用小木条儿围成的鸡窝,迈着缓慢而高傲的步子,瞪着圆溜溜的眼睛,昂着头,挺着胸,看看这儿,瞅瞅那儿,嘴里还发出轻微的咕叫。柳婆知道它们是饿了,返身从屋子里扯过鸡食盆,舀上些玉米面,再抓上两把前一天剁好的菜,用棍子在里面搅了搅,就将盆子放到院子当中,让那些鸡们去吃。
这时的山筒子里有一片氤氲的雾在弥漫,在山沟的深处荡漾,显得大山既高大又深远,看上去平添了几分神秘和空旷。这是一天当中最靓眼也是最恬静的时刻,柳婆很喜欢这样的早晨。
饭很简单,是由两块地瓜和一盘咸萝卜条儿构成的,老太太简单地吃了一口就饱了。吃饭的时候她没有放桌子,而是和鸡们站在院子里一起吃的。那些鸡比老太太吃得快,一叨一叨,一惊一惊的很是机敏。老太太就不行了,她的动作很慢,很迟缓。她站在那里,边吃边瞅着这些鸡,辨着这些鸡今天哪个能下蛋。老太太看得是很准的,不用摸就知道哪个鸡有蛋,能看个八九不离十呢。
吃完饭,简单地拾缀了拾缀,太阳就出来了。山里的太阳和城里的不一样,山里的太阳是鲜亮鲜亮的,红彤彤的纯洁。像少妇在夜里被男人羞红了的脸,腼腼腆腆地从山的垭口处出来了。那太阳每天都是从那个垭口处出来,像是从山的垭口处生出的一个火红的肉蛋。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并不热,像是在夜里耗尽了能量,没有一点儿的精神和热情,就那么赤裸裸羞答答地什么都没穿就出来了,像是假的,或者是一块透明的彩色剪纸,就那么稳稳当当地贴在了那个垭口处,看上去与山里的景色不很协调。好在那张脸是红的,当她跳出山垭口的瞬间,猛的喷出了一口血,把整个沟筒子都溅红了。那山沟子的每一处一下子就被镀上了一层金色,辉煌煌地灿烂。
柳婆出了屋,走出了院子,来到乡路上,她的身边不知什么时候还跟着一条狗,那狗是黄色的,老太太叫它“大黄”,是吴老二家的,吴老二走了,狗留了下来。
柳婆走着,手里柱着拐杖,那拐杖是一根粗藤做的,已经跟她好多年了,磨得有些乌黑发亮。老太太走着,狗也走着,她的身旁是一条小溪,可这里的人不叫小溪,叫河,而且还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香水河,河水是香的吗?不知道,就这么叫下来了。由于是初春,天儿还凉,那河水冒着淡淡的雾气淙淙地流着。河道不是很宽,那流动的水拧着一股劲儿,那劲儿拧得很美很自然,犹如乡下的女孩子梳的一股股辫子,既柔美又质朴。
河水是从山里流出来的,河的两侧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是山坡住着人家。整个沟筒子也就十来户人家,打远望去就像十几贴膏药,很不规整地贴在那里。眼下一家家的房子都没了主人,没了炊烟,也没了烧草木灰的味道,时而能见到几只鸡或狗在院子里转,也是无精打采。
柳婆走进一家院子,院子很破,到处扔的都是柴草,老太太就嘟囔,这个吴老二,从没见他家干净过,这哪儿像过日子的样儿,到城里这么多年也还是这么邋。说着,帮着拾缀了一下,就进了屋子。屋子很破,同样也很脏,屋的炕上地下有那么几只鸡,听见来人就到处乱飞。老太太说,造反了,造反了,人窝成鸡窝了,这哪儿是人住的屋子。说着从一个装有干玉米的麻袋里抓了两把玉米扬到地下让鸡去吃。那些鸡见了吃的都奋不顾身扑了上来,老太太又扫了眼屋子,皱了下眉,离开了。那狗也跟老太太走出院子,老太太说,不在家看家跟着我干吗,那狗好像是明白了,转身回了院子。
这时整个山峦已经是阳光普照了,阳光一出来那晨露就慢慢地退下去了,一切都沐浴在阳光里。老太太往前走着,同样接受着阳光的照耀,这时的太阳不是那么红了,像似有些金黄,映在老太太的白发上银光闪闪的。河水的寒气也没了,只剩下了汩汩的流水声。
过年的这些日子,柳婆家没有断人,拜年的,送吉祥的,晚上陪老太太唠嗑睡觉的,男男女女在她的眼前晃动,开始的几天还行,渐渐地她心就烦了。好像不是在自己的家,仿佛是在别人的家过年了。当然,柳婆很过意不去,很感谢他们,人家给你拜年你有什么烦的呢?这么多人来陪自己,给自己磕头,拿好吃的,讲城里的故事,她当然应该高兴。可老太太就是高兴不起来,她瞅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不像先前那样有亲切感了,仿佛打远方来了亲戚,她们说的不是山沟子里的话了,老太太有好些听不习惯,那味儿也不对,怎么就那么分生呢?可柳婆还是听,不仅听,还跟着笑,笑的时候嘴是空空的一个洞,没有声音,还一个劲儿地点头,心里却在想,外面再好也不如家呀。这大山里虽说没有城里那么多的人,没有那么多的车,没有那么宽的马路,剩下的什么都有,花儿呀草儿呀牛呀羊呀山山水水呀,哪样儿不是那么真真切切,实实在在。柳婆虽说从没进过城,可听说过,年轻时听丈夫说过。
那条狗又跟了上来,柳婆看了一眼,嘟囔:你怎么又来了。狗摇了摇尾巴,像是在说:还是让我跟着你吧,咱俩是个伴儿。于是,就跑到老太太前面去了,紧接着又毫无缘由地叫了两声,那群山听到狗的吠叫,也跟着吠叫起来了。
沟筒子由金黄变得白亮了,这时的太阳不是红色的,也不是黄色的,是亮白色的,也不像刚才升起来那么轮廓清晰,而是模模糊糊的耀眼了,像有无数根针,风风火火地刺来,扎向你的瞳孔。河水依旧是哗啦啦地听着悦耳,像是流到心里凉爽爽畅亮亮的。柳婆来到河旁,一只手柱着拐杖,勾着腰,将另一只手伸向水里。新的一年这是她第一次摸这里的水,清清的,凉凉的,爽爽的,通过手传到了她的心里。老太太用手撩了一把,喝了,又撩了一把,又喝了,水是甜的,冰甜冰甜的,仿佛真的有一股香呢。那狗也停下了脚步,耷拉着粉红色舌头,看了眼柳婆,又看了眼河对岸,吠叫了两声。
河对岸是一面笔直的峭壁,峭壁上挂满了花花绿绿,老太太看不清是什么,可她知道,那是村里人给狐仙太爷太奶和黄仙太爷太奶上的供。
柳婆很喜欢这条河,特别是这河水,清亮亮地养了他们多少代:喝水、淘米、煮饭、洗衣服、洗澡等等,都指着这条河,可源头在哪儿没人能说得清,就那么流个不停。
过了一个山梁,来到了马寡妇的家门前,老太太心想,没有男人就是不成,看这家造的,还能住人吗?又一想,也确实不住人了,马寡妇过年回来,除了在她家住了两宿,大多的时间都是在村长家过的。柳婆没有进屋,马寡妇跟她说过,这房子里什么都没有,好用的都搬到村长家去了,这房子将来要卖,可老太太还是围着房前房后转了一圈儿。然后坐在院门前的一块青石上歇脚儿。
老太太在想,一晃又是一年,太快了,昨天村里还热热闹闹的,大人喊,孩子叫的,今天就剩下她一个人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村庄里只有她一个人,好像这个大山里只有她一个人,别人都不存在。太静了,太寂寞了,不知怎么,人多了她烦,人少了又觉着空旷。
狗又走上来,柳婆伸手摸了摸它的皮毛,很光滑、毛亮,那狗很听话,回头用舌头舔了舔老太太那有些发亮的手背,老太太说,就你好,不嫌这个家穷。说着,又站起身,继续往前走。
过了马寡妇家就是村长家了,两家是邻居。柳婆看了一眼,村长家的院子就是比别人家的大,院门是铁的,锁着的,里面没有鸡没有鸭也没有狗,空荡荡的一个大院子。这个大院子原来是大地主周大癞家的,周大癞早被打死了,现在住的是村长。听人说,村长在城里买了新房,这房子也不想要了,要带马寡妇到城里住了。柳婆特意看了一眼,心想,这么好的房子就不要了,败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