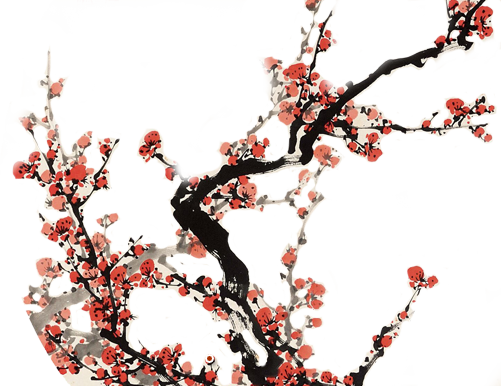




菊 花 忆
张 冰
北方的乡村一进初冬就没有什么景色了,每下一场小雪儿天气就凉了几分;田野里灰蒙蒙的,树枝上沾着的几片黄叶,恋恋不舍地落下了;侯鸟们急忙地迁移到南方去了,剩下几只麻雀在房前屋后呻吟着:“什么时候才能熬过这鬼天气呢?”
但在我家院子的那两盆秋菊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似的,开得更加旺盛了。黄色的花朵沾上洁白的雪儿,显得格外鲜艳了。
从我记事那天起,母亲就爱摆弄一些花儿。她把家里闲置的一些坛坛罐罐盛满了土,栽上一些花草让我们欣赏着。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出名的花儿,那两盆秋菊还算不错的。每年一开春母亲就忙碌着,好像是一种寄托似的。
我读中学的时候,家里的生活比较拮据,经常靠表舅和二姨家接济。父亲有时心情不好,时常把花盆砸碎了,花儿扬得满院子都是。好在都是些草本花儿,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父亲过几天消气了,母亲又种了一茬,尽管稍晚了一些,秋末冬初也能闻到花儿的芳香。
在众多咏菊的诗词中,母亲最喜欢明代诗人于谦的那首《过菊江亭》的诗:“杖履逍遥五柳旁,一辞独擅晋文章。黄花本是无情物,也共先生晚节香。”
母亲喜欢菊花是为了调解心境的。她6岁的时候,我外婆就去世了,她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太姥姥家渡过的。舅姥爷(母亲的舅舅)待我母亲像亲女儿一样,她与我二表姨一起进了私塾读书习文,母亲的学业很出色,她能背诵《百家姓》、《千家诗》、《三字经》,还能通读《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名家名著。在那个年代,母亲纯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也是远近闻名的“小才女”。
母亲对我说,从周朝至春秋战国的《诗经》和屈原的《离骚》都有菊花的记载。有诗云:“朝饮木兰之堕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菊花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家原是一个大家族,曾祖父带领祖父及父辈们艰苦创业,除了耕作农田外,还开垦了百亩盐田,创建了“辽东湾盐业商行”,白花花的食盐销往全国,包括延安等革命根据地,也通过海上销往东南亚及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张氏家族”在本地区赫赫有名,也谓远近闻名的“资本家”。
一九三四年父亲与母亲结婚,那时的家业正是旺盛时期。父亲号称是张氏家族的“三少爷”,在外人眼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日本占领东北后,家族的盐业被日本人霸占了,美其名曰叫作“合作经营”,其实都是日本人说了算。小鬼子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以“通共”的罪名将我家的盐田没收了,从此张氏家族彻底破产了。
一九四六年初,以我父亲为首的叔侄六人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心不推翻国民党政府不回家。
菊花属于草本植物,她分地上茎和地下茎两部分。花期过后,地上茎大多都枯死了,次年春季由地下茎发生孽芽。母亲每年开春就忙活给盆里的发芽根浇水施肥,期盼立秋时节能闻到菊花的清香。
父亲参军后,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在家度日,那时,大哥张耀千10岁、二哥张耀田8岁、姐姐张素仙5岁、三哥张耀文2岁,还有母亲怀里怀着的四哥没有出生。
那个年头,可谓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民不聊生。一九四七年的冬天,未满6岁的姐姐就饿死了。听母亲讲,那一天格外寒冷,外面飘着雪花,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姐姐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了。她说了一声:“妈妈我饿”,母亲喂了一口水她就咽气了。那年大哥才11岁,骨瘦如柴,没有力气抱着姐姐,埋她的时候,哥哥只好拽着姐姐的两条腿在雪地上拖着,葬在房后的壕子里了。据哥哥讲,当时把姐姐后脑的头发都拖掉了。
每每想起母亲讲述这段悲惨遭遇,我不由得仰天长叹,肝胆欲碎,泪如泉涌。什么人能承受了这样凄凉的场面呢?那是我的母亲,我那未满32岁的母亲……
一九四八年初,正是国共两党“拉锯”的时候。为了争夺营口这个战略要地,两军进进出出又出出进进,周边的老百姓更是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听母亲讲,左邻右舍的几个村几乎天天都在死人,饿死的孩子随处可见。
这一年,我四叔来到我家,跟母亲说:“这样下去,几个孩子都得饿死,我带耀田出去要饭吧。”母亲没有答应。后来在四叔的再三劝说下,母亲为了二哥活命只能默许了。
二哥那年10岁。临走之前,母亲给他缝改了一件旧衣裳,在胸前做了一个“大兜兜”,告诉二哥:“要到东西就往大兜里装。”二哥说:“妈妈,我会要好多好多东西的,带回来给你吃”。
临走的那天,母亲再三嘱咐四叔,一定要照顾好孩子,四叔也表态:“宁可我受苦,也不让孩子受委屈。”母亲含着泪水,送到村口,望着远去的四叔和二哥的背影,久久不肯离去……
那一年,母亲身怀八个月的四哥就要临产了。大哥跟母亲说:“妈妈,咱俩不出去要饭,在家就得饿死。”母亲一把抱住哥哥,放声大哭:“大儿子懂事了。等妈妈生下你小弟弟后,我们娘仨一起走。”
一个月后,四哥降生了。那时家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母亲生下四哥的第六天,只好忍着身体的疲惫及疼痛,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带着哥哥离开家乡,蹒跚向北逃生。
听母亲讲,当时天气很冷,产后的血水一直流到脚后跟。那种痛苦是常人无法忍受的。
走了大半天,到了大石桥。当时的大石桥火车站前,来往的人比较多,有做买卖的、有赶集的、有要饭的、有卖孩子的……一片凄凉的景象。
大哥穿着破衣烂衫,饿得躺在马路牙子上。一位赶大车的中年男子,见到哥哥的样子,用脚踢了一下哥哥的脑袋说:“这孩子死了吧?”母亲说:“没死,是饿的。”于是,那位好心的男子,从车上的马槽子里拿出一小块豆饼送过来,母亲把那块豆饼泡了一些水喂了哥哥,哥哥才缓过来气。
这时候,我远房的一位舅舅叫冷守成,他在火车站前拉小活,看到母亲悲惨的样子,便劝母亲说:“表妹呀,还是把怀里的孩子送人吧,让孩子有个活命吧。”
那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母亲想:“自己的亲骨肉,怎么能送人呢?”。又想“刚生下几天的婴儿,没有奶吃,早晚也得饿死”。在表舅的劝说下,母亲只好把怀里抱着的四哥送人了。
四哥被抱走的那一刻,母亲抱着大哥放声大哭,当时围观的人无不伤心流泪。
母亲说,菊花是花中四君子之一。她最可贵的是不与春兰争艳,也不跟夏荷竟辉,更不与牡丹媲美,只是在百花凋谢的时候,解除人们对悲秋的失意感罢了。
离开了大石桥,母亲带着哥哥一直往北走。娘俩儿,破衣烂衫、风餐露宿,走一道、要一道,人间疾苦尝到了尽头。
那年深秋,母亲带着哥哥乞讨到海城县境内。一天傍晚哥哥突然发高烧不省人事,母亲把他抱到一家门前的大榆树下,用手扒榆树皮,一口一口地嚼着喂哥哥。过路的人都摇头:“这孩子肯定不行了。”母亲哭着喊着,没有一个人应声的。
就在母亲求生无望的时候,村里的一位好心人端来一碗玉米汤糊过来了,对母亲说“让孩子喝了,看能不能救活。”母亲趁热把汤糊喂给哥哥,过了好一会儿,哥哥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经过母亲六七天的照料,哥哥总算活过来了。
一九六五年春天,哥哥参加全省四级干部农业拉练会,正好来到他讨饭时的村庄。他看见那棵大榆树时放声大哭。在场的人都莫名其妙,省领导上前问他哭什么,哥哥如实把他当年随母亲讨饭时的情景叙述了一遍,在场的人都落泪了。
据母亲讲,哥哥拉练回来,大病三天三夜,这里面包含着多少童年、少年的心酸与苦辣呀。哥哥的心情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父亲参军后,经历四次大小战役,著名是辽沈战役。在攻打锦州时,父亲所在的连队部署在塔山,负责阻击南线增援锦州之敌。据父亲讲,国民党军从陆地、海上展开了阶梯式的轮番进攻,上有飞机轰炸。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山岗。经过四天四夜激烈战斗,确保了锦州战役的胜利。塔山阻击战伤亡惨重,我父亲所在的团只剩下二十几人。
全国解放了,父亲也复员了,母亲领着哥哥回家了。过了不长时间,四叔也回来了,但只是他一个人回来的。我二哥哪去了?母亲不停地追问。四叔嘴里总是吐出两个字“死了”。母亲有些不相信,整天以泪洗面。
我四叔是一个老光棍子,一辈子没娶亲,晚年跟村里的一个小寡妇打伙过了几年。用当时的话讲,四叔就是一个游手好闲之人。
过了好多年,老家捎来信儿说四叔病危,母亲去看他。那时四叔已经不省人事了,母亲又追问他:“老四,你都这样了,快告诉我耀田真的死了吗?”四叔慢慢地缓了一口气,用微弱的、几乎让人听不清的声音说:“对不起三嫂,耀田让我卖了,卖了6块大洋。”母亲急切地追问,“卖到哪里了?什么地方?”“卖到西丰县了。”说完,四叔就咽气了。
母亲回家后,整整病了一个月。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她总是默默地流眼泪,母亲失去的太多了。
一进入深秋季节,其它的花儿都凋谢了,唯有那两盆秋菊在庭院里掩映着。哪怕是花朵开的不那么娇艳,母亲总是耐心地侍候着。一次我随便摘了一小朵,母亲不高兴了,便对我说:“天气这么冷,开一朵花不容易,哪能说摘就摘呢。”我理解母亲的心思,从那以后再也不摘花儿了。
我上大学走后,总是惦念着母亲和她栽的那两盆秋菊。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母亲在庭院里侍弄花儿,突然晕倒了不省人事,我被惊醒了,出了满身冷汗。第二天也没心思上课了,总想请假回家看看。后经同学解梦说:“做梦都是相反的,老娘保证没事儿。”我的心儿才慢慢地静了下来。
放寒假回家,那两盆秋菊已经凋谢了,但叶片还是绿绿的。母亲对我说:“今年的菊花开得又大又鲜艳,还给邻居移栽几棵呢。”我怕母亲太劳累了,不想让她再摆弄花了。一次,我到商店里买了几束塑料菊花插在花盆里,母亲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过了几天塑料花不见了,我仔细找了找,让母亲放到装粮的库子里了。母亲说:“菊花还是真的好,在寒冬的季节,她蕴藏着春的气息,又能解除苦闷的心境。”我十分理解母亲的心。
我要毕业的那年暑假,几个同窗好友回乡后约到盖州市杨运乡同学家游玩,也算避暑吧。
杨运乡位于辽南中部,属于长白山末脉。那里山清水秀,气候宜人,可谓避暑的好去处。每到夏季多有学者、骚人到那里休闲渡假或吟诗作赋。
而不料的是,我们一到杨运乡天气就变了:天刚刚变黑就下起了小雨,后来变成了中雨、大雨……山洪爆发了、铁路冲断了。一时间整个山村被洪水冲刷得干干净净,我们拼命逃到山坡上,没来得及跑出的人大部被洪水冲走了。
杨运发大水的消息迅速传开,母亲知道后,整天以泪洗面。半个月过后,我与另一位同学走出了灾区,“平安”地回家了,但母亲的右眼永远地失明了。
两盆秋菊发芽、开花,开花、落叶,一晃儿几年过去了。我毕业被分配到当地的一所中学教书,后又调到区里工作。那时工作比较忙,但我每次回家都细心地帮助母亲拾掇拾掇那两盆秋菊。临走时,母亲总是念叨着:“不要辜负国家,要好好工作……”她拄着棍子,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已经看不见我的影子了,还不肯回去。
有一天,我到乡下研究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工作,顺便回老家看看母亲。母亲拿着眼镜对我说:“我的老花镜掉了一个腿,没有它我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对母亲说:“明天我给您买副新的。”母亲笑了笑说:“好,好。”可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多过去了,母亲也没戴上新的老花镜……
1994年3月一天,冬季的凉意还没有完全消失,村里人捎信来了,说母亲病了,病得很重。我当时惊呆了,一句话也没说,驱车就往家里赶。
到家后,母亲已经昏迷不醒了。医生诊断是“脑出血”,经过多方抢救也不见好转,十五天后,母亲就去世了。我手里拿着母亲那副掉了腿的老花镜,愧疚得如箭穿心一样……对母亲的遗憾是终生的遗憾。
咳,想起这些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去年,熊岳望儿山建了一座“慈母馆”,我花了近半年的工资将母亲的画像刻在慈母馆显著的位子上,并亲笔书写“香火暖母寒”五个大字。每年母亲节,我便带着女儿到慈母馆给母亲敬香,让母亲在九泉之下永远享受人间的香火,因为母亲的一生太冷了……
母亲离开我也有两年多了,那两盆秋菊也不知去向了。昨天听村里来的人说,哥哥在母亲的墓前载了两棵长青树,又种了一些花草儿,我心里很高兴。做后辈人了,在老人墓前放一些她生前喜欢的东西,不管是有用没用,也算尽了一点孝心吧。
想到秋菊,更思念我的母亲。她给我的太多了,而我还给她的太少太少……
作者简介
张冰,字耀松,笔名东南,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祖籍山东蓬莱,1957年10月生于辽宁省营口市郊区。先后担任过中学语文教师、营口市老边区广播电视局局长、营口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营口市档案局局长兼党组书记、营口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期间,兼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中国乡土文学协会理事、营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营口市诗词学会会长、中国·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理事长。现已出版诗集《晨情》、《芦堂吟草》,散文集《东南方的白云》、《芦苇》等,其中散文集《芦苇》荣获辽宁省二十世纪“丰收杯”三等奖。其传略被收入《中国当代艺术名人大辞典》、《中华人物大辞典》、《中国人才世纪献辞》、《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等。